记者 |
编辑 | 崔宇
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常态。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一直面对着多重挑战,新冠疫情加剧了此前许多国家财政赤字的遗留问题,各国都在公共政策方面面临艰难选择。从平权运动到俄乌冲突,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时刻待发。从欧洲到美国,公共舆论场的撕裂已深刻地重塑了各国的政治生态。面对一个充满极端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学家可以给出怎样的药方?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John Kay)指出,诸多矛盾的背后,一直在加剧极化和冲突的正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逻辑。与经济学界重视量化的习惯不同,约翰·凯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并非所有情况都可以被量化、被预知,我们能掌握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我们处于“未知的未知”之中。但同时,生存并不需要“最好的”解决方案,只需要“足够好的”解决方案。
约翰·凯的这些想法不仅源于他作为经济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更来自他在为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担任经济顾问的一手经验。现年74岁的约翰·凯是知名英国经济学家,曾任牛津大学萨伊德商学院首任院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伦敦商学院教授,现任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研究员、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2016年,他担任苏格兰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他还曾为英国政府商业、创新与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简称BIS)主持对股票市场和长期主义决策的审核。近年来,约翰·凯专注于面向大众读者写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提供经济学视角,著有《市场的真相》等多本著作,其著作先后获得过《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和彭博社的年度图书等奖项。
2020年,在新冠疫情刚刚席卷全球的初期,约翰·凯发布了与人合著的两部专著。一部是与英国前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合著的《极端不确定性:如何为未知的未来做出明智决策》(Radical Uncertainty: Decision-making for an Unknowable Future),对一度流行的市场万能论和货币政策万能论都进行了批判。另一部是与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合著的《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Greed Is Dead: Politics After Individualism),力图回答关于政治极化的热点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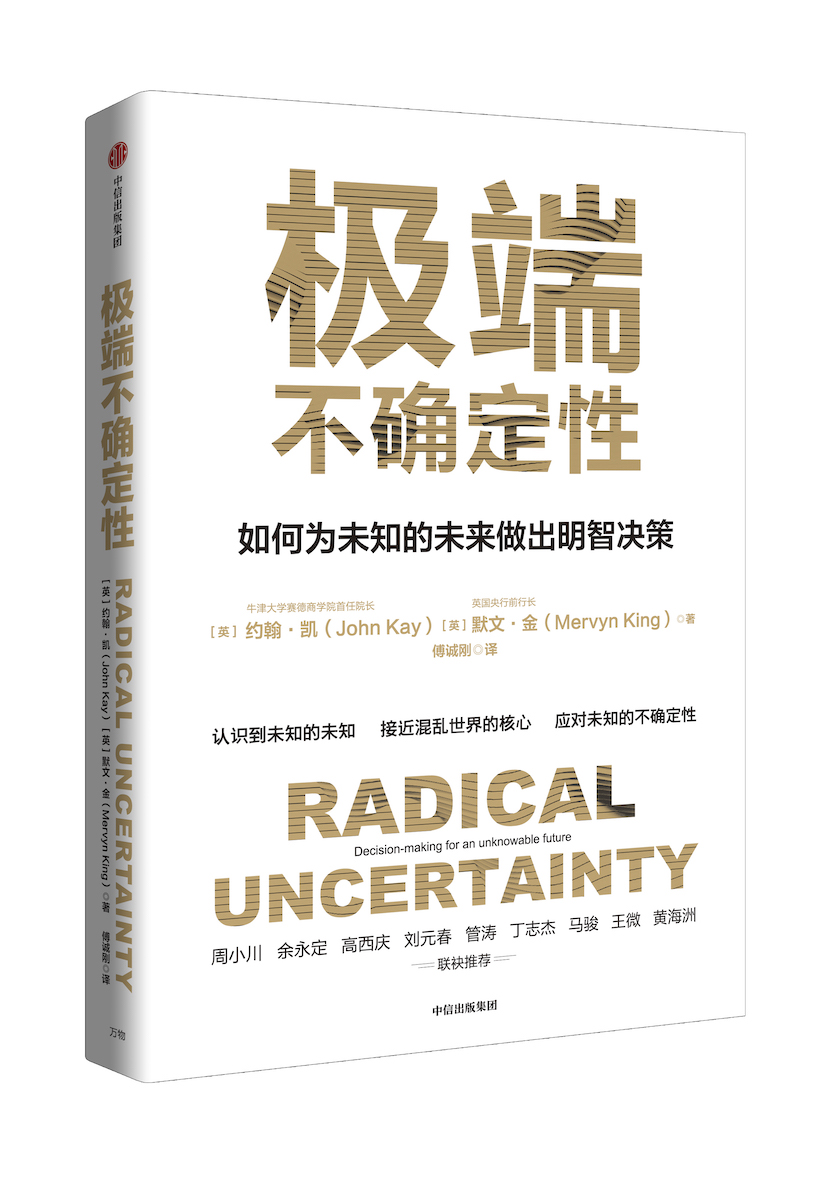
日前,界面新闻就两本新书的相关议题远程专访了约翰·凯。约翰·凯在专访中表示,他自认为在英国政治光谱中属于中左派,然而“如今的政治里似乎已经没了我们这种人的落脚之处,因此,写书也相当于一种公开的宣言,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约翰·凯认为,极端个人主义通过不同的表现渠道,最终导致了“传统政治的崩溃”。在表现式个人主义、占有式个人主义及其催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潜移默化下,右翼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右翼,左翼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中的左翼。前者只能通过“受到左翼政治的威胁”团结在一起,后者则轻视了经济与收入分配的重要性,投身大都市精英更为关注的性别、种族、气候变化等议题。以英国政坛为例,约翰·凯指出,历史上曾经坐拥工人阶级票仓的工党正是因此在2019年大选中把这些选民送给了保守党。

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身份政治都“不足以成为未来的真正出路”,人们又该在何处找到自己的归属?专访中,约翰·凯谈及了他的新书与当下的政治极化困境,并将社群主义作为解决方案。以近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逝世为例,他认为,伦敦市民吊唁的场景“以强有力的方式表明了诸如女王这样的象征符号相当有利于打造认同感以及团结”。作为在爱丁堡出生长大的苏格兰人,约翰·凯长期关注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权力动态,对于近年来的独立呼声深有感触。他表示,正是在“共享的认同”中,个体得以建构起共同的社群,得以通过参与社会网络中丰富的群体活动求得自我实现。
以下是界面新闻对约翰•凯的专访实录,内容经过编辑:
左右对立的瓦解和传统政治的崩溃
界面新闻:我想从英国社会近期的一些戏剧性变化开始聊起。首相换届、女王去世等政坛大事件就发生在短短一周之内。你对这些动荡的观感是什么?
约翰·凯: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这些话题的共有元素,那就是传统政治的崩溃。左右派之别,或者说两极对立,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主导了英国以及欧洲的政治生活,自1990年代柏林墙的倒塌以及苏联从东欧撤出以来,这种政治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走向了瓦解。
据我观察,以往简单的左右两极对立已经不再有多少意义了。其特点是,作为一种严肃学说的左派思想已经销声匿迹,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一现象同样适用于右派。与其追问“令欧洲诸多右翼政党团结在一起的究竟是什么”,还不如说,分属背景各异的人群由于恐惧社会主义而走到了一起。生意人、自由至上的个人主义者、珍视传统的保守派以及某些好战分子,这些人原本没有多少共同点,唯独都受到了左翼政治的威胁。
稍加留意便可发现,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政党运作模式各不相同,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这些国家的派系对立态势已经不同于以往。如此一来,许多投机分子也就有机可乘,他们遍布于政治光谱各处,如约翰逊和特朗普就属于其中成功登堂入室的极端个案。与此同时,政党成员身份的意义也坍缩成了极端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小团体。
就英国政坛而言,工党在2019年英国大选中出现的问题不单属于2019年,它具有长期性的根源。工党现在已经成了大都市精英人士的联盟,聚焦于诸如社会性别、种族与性取向之类的议题,此外还有环保问题。这已经偏离了左派的传统领域,他们本来关心的是经济与收入分配等议题。所以现在工党的处境很尴尬。2019年的选举结果固然是其体现,但工党一面在大都市中产区域攻城拔寨,一面失去其传统核心支持者的趋势却已持续50年有余。传统上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在英国已经崩溃了,在其它一些欧洲国家以及美国也类似。
在我看来,这就是现今政治动荡的根源所在。目前还看不到走出这种局面的捷径,除非有人愿意下功夫去重构政党,但短期而言这还不太现实。即便有人去推动了,不同国家的落实方式也不会一样。
界面新闻:如果说西方政治中传统的左右派分野已经不再能反映现实,那你会建议怎样的新式划分方法?我们所面对的全新现实究竟是什么?
约翰·凯:我不知道,我想英美现有政治架构下的“胜者全得”机制易于形成和加强两党制。我觉得未来可能在于不同政党团体的联盟。这种模式在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运行得还不错,譬如荷兰,一些北欧国家的情况也还行。不过最近瑞典的一连串事件(编者注:2022年9月的瑞典大选后,右翼政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以微弱优势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其中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获得73个议会席位,成为瑞典议会第二大党)构成了一大反例,我也有些怀疑自己原本的看法了。
界面新闻:英国保守党是英国政体之下的赢家。它掌权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但近年来也经历了非常频繁的党首更换。我感觉脱欧前后的英国保守党完全是两幅模样,不知你是否同意这个判断?这是否意味着保守党也处于转型的关头?
约翰·凯:是的,我认为确实如此。英国脱欧一事,除开其它方面的损害,也确实在保守党内造就了一个很奇怪的现状,一些贤能之士离开了,另一些则从部长级职位上退了下来,我觉得保守党多少还有足够的余力来度过这一难关,但这尚待观察。根据现在的局面,保守党想输都难,毕竟工党已经丢掉了许多支持者,无论在英格兰北部、苏格兰还是一些小的乡镇都是如此。
我是苏格兰人,比较关注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以及独立相关的争议。我最近还写了一篇讨论腐败和信任指数的文章,透明国际和皮尤价值观调查经常做这类工作。如果你熟悉这些调查的话,不难发现在其中排名靠前的多是一些西欧小国。在清廉指数前十的国家里,人口超过千万的国家只有荷兰。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对腐败的感知,二是人们是否觉得大多数人一般而言都是可信的。由此不难想见,丹麦、芬兰、挪威会名列前茅,而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则被远远抛在后面。英国和德国的表现只能说尚可,但比起北欧国家还是有显著差距。
更大的问题在于通胀的长期影响
界面新闻:过去五六年对于苏格兰也别具意义。尤其是苏格兰独立与英国脱欧的两次公投。我读到一篇你发表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前夕的文章,主旨大概是一个既有苏格兰又有欧洲认同的英国人如何乐于维持现状。但文章发表之后的两周之内英国就公投离开欧盟了。英国脱欧对你个人而言有何意义?你认为英国脱欧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
约翰·凯:无关紧要,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不过我也没发现英国脱欧对我有什么很正面的影响。有若干比较琐碎的变化,诸如过关时查验护照要排更久的队,在英格兰和法国之间寄东西比以前也要难一些。我认为商业所受的影响不算严重,但也几乎全是负面的。我在一些小企业上投了些钱,对这个领域也多留了些心,这类企业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网上向全欧顾客销售的。英国脱欧对他们的确非常不利,小企业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是一种不明智的自残行为。
界面新闻:脱欧公投已经通过六年有余,后来又出现了诸如新冠疫情、乌克兰冲突、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等一系列全新的压力。在你看来,英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约翰·凯:我认为问题不只一个。就像你刚才所描述的,有一系列的问题,而其中最迫在眉睫的则显然是通胀,但通胀本质上又是个暂时性的麻烦。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今的通胀高峰究竟会产生何种长期影响。这一点我们可能需要等个一两年才能看清。欧洲的能源供应,以及程度稍轻的食品问题,都是可以自行消退的,无非是早一点还是晚一点的问题。但我们也不知道恢复的速度具体能有多快。
界面新闻:英国脱欧是否弱化了工薪阶层抗风险的能力,也使英国在应对全球危机时处在一个更加脆弱的位置?
约翰·凯:我不打算说得太夸大,只能说脱欧无益于缓和局面。它不能为解决问题的提供资源。
界面新闻:英国经济当前问题的源头主要在哪里?
约翰·凯: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源头。我想,自从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就一直没有把经济管理得很好。但我们也很难说别的国家就做得比英国出色许多。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理解2008年以来的一系列金融和货币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

个人主义无法为社会提供解决之道
界面新闻:《极端不确定性》与《贪婪已死》都是发布于疫情初期的专著。在那个时间点上,你们是否感受到了某种需要发声的紧迫性?
约翰·凯:若干年前我发现,自己最擅长做的事还是以通俗易懂的话来阐释一些相对复杂的经济理念。坦白讲,我不太喜欢写学术文章,面向大众写作(的过程)要有趣得多。我希望能为那些喜欢读哲学、科学或历史类通识读物的人提供一个经济学的视角。这也是我与保罗·科利尔合作以来就一直在用功的主题,即讨论英国政治的现状,也包括我们之前聊到的传统政党结构崩溃等问题。以《贪婪已死》这本书为例,当时成书的最大原因在于对2019年英国大选以来的政局的关切,我们希望能为自己偏好的那种政治发表一份宣言,讲清它应当如何演化以及向前发展。我们自认为在英国政治里大致倾向于中左派,如今的政治里似乎已经没了我们这种人的落脚之处。就此而言,写书也相当于一种公开的宣言,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以及提出哪些方面还需要重思。我们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个人主义。一种是经济个人主义,它以极端化的方式刻画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种则强调围绕社会性别与性取向等议题的、数不胜数的身份认同,但两者都不足以成为未来的真正出路。如你所知,《贪婪已死》这本书最大的主题不如说是强调社群(community),它不打算再激化个人与国家间的种种代理者的对立。
界面新闻:如果说是为了不再激化对立,那在你看来,社群应当在个体公民与国家之间扮演怎样的中间角色呢?
约翰·凯:社群可以有许多种类。我主要支持的是政治社群,它关乎权力和政治的组织,所处的层次远低于由伦敦主导的那些结构,这是英国的现状。我刚才着重谈了商业,商业社群的确是我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社群,但我并不打算以一种还原主义(reductionist)、个人主义的路径来分析人们的相关行为。
界面新闻:能否详细谈一谈个人主义为什么无法再为我们的社会提供解决之道?
约翰·凯:我甚至不确定个人主义是否曾经算是解决之道。过去两三个世纪以来,西方在经济上的成功实际上是基于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发展,以及人民的通力合作。在下一本书里,我还将讨论更多这一方面,我会分析为什么亚当·斯密的小作坊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在这之后是工业革命的发端,生产的流程被打碎为了诸多分立的环节,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世界就是如此。我最爱用空中客车当例子。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单独知晓如何这样造出一架飞机,要一万个人齐心协力才行。过去两个世纪尤其是上个世纪以来,载人飞行最初还只是一小部分人脑中的梦想,而今我们已经有了能搭载500名乘客,航程达2万公里,足以环游世界的飞机。这是合作带来的惊人壮举。
但单单依赖个人主义或是国家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的社会是通过诸多组织来运作的,它们既非个人也非国家。我们之前谈到了一些小国的成功,以及它们所培育的高信任度与低腐败。这些就属于我所谓的中等规模社群,信任度高且社会资本充裕,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成功并不来自国家指令。个人主义和中央指令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一点必须要理解清楚。
界面新闻:新冠疫情的发生是否对写作产生了影响?
约翰·凯:对我书中的论证影响并不太大。但疫情的确也凸显出了不同社会在应对措施上的多样性。例如有些国家的对策强调权威与效率,美国的对策更具个人主义色彩,欧洲国家如瑞典、丹麦等则比较务实和渐进,而这也表明个人、社群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呈现出繁多的模式。
理想的社群基于正面的“共享的认同”
界面新闻:我们之前还提到了不同类型的社群。你如何定义社群?你会如何描绘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群?
约翰·凯:我想,社群的典型特征在于人们对社群有着一种共享的认同。你在一开始曾提到女王去世,这种事在英国就足以产生某种类型的团结。它以强有力的方式表明了诸如女王这样的象征符号是相当有利于打造认同感以及团结的。
界面新闻:伦敦人排队吊唁女王的浩大声势的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你认为自己是一位“王室主义者”(royalist)吗?
约翰·凯:我想我还是愿意保留君主的,这套体制看起来运行得还不错。人们暂时还看不到显而易见的更佳替代选项。因此我对现状基本是满意的。虽然有愿望成分,但我还是相信查尔斯在成为团结国民的符号这一点上能做得和伊丽莎白一样好。
界面新闻:在你看来,伊丽莎白女王为英国社会留下的最重要一笔遗产是什么?
约翰·凯:我认为是国民对同侪以及英国的稳固认同,它造就了对英国这一实体的感知。不论是我刚才提到的苏格兰独立问题,还是诸如英格兰北部与伦敦日益离心离德的问题,都无法归结到独立或者类似的诉求上。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传统的政治结构已趋于崩溃。君主乃是人们的英国认同的一部分,不过这个部分的力量已经没有历史上那么强大了,人们对“英国性(Britishness)”的感知也随之下滑。
界面新闻:你刚才谈到了共享的认同对于构建社群的重要性。但“共享的认同”可以意指很多东西,例如共同的国籍、种族或是性别等等。在你看来,目前是否有我们需要加以关注的、足以构建起强有力社群的核心认同?
约翰·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会自视受害者然后以此来组织社群。一个人以自己出生的地区来定义自己,这本身没有大碍。至于种族方面,对于美国黑人在过去受到的不公待遇,有两种不同的回应方式,一种认为黑人要构建自己的社群,另一种则主张黑人应融入更广大的社群。我当然倾向于后者是更好的解决方案,但双方一直都在争论。其后果是,支持前一种方案的人主张自己属于黑人社群,在历史上曾受过不公对待,沿着这条路线,基于社会性别、身心障碍或是性取向等等的受害者群体没完没了地涌现出来。这是构建社群的思路之一,但它也多少遮蔽了基于另一些共享认同来建构社群的路径,如国家或是商业性的社群,又或者是特定地区的居民所构成的人群。
界面新闻:依照你的定义,共享的认同应当关乎国家、产业或是我们所居住的地域,而非种族和性别吗?
约翰·凯:是的,它涉及团结与合作。因为在历史上国家、产业和居住地都曾取得过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硕果。国家间的移民史在此算是一个强有力的历史例证。移民总体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源于移民群体具有善于沟通、能对更广大的社群做出贡献等美德。
保持孤立并坚守自身认同的移民群体则会起反作用。就此而言,主张社群关乎共享的认同,不等于说所有的共享认同都是正面的。例如“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就不属于正面的共享认同。它们虽然也是社群,但作用基本是消极的,因为它们的认同趋向于走极端,并倾轧其它群体。我想,这背后的根本要害在于合作与竞争通常是混杂在一起的,经济与国家的成功均仰赖于此。我们总是需要在竞争与为共享的目标而合作这两者之间维系一种微妙的平衡。处理好这种平衡,乃是我们经济成功的秘诀之所在。
所谓毁灭性的社群,是指那种在很大程度上专与其他社群作对的社群。美国的种族以及其它一些问题就与此相关,我们刚才已谈过了两种化解种族难题的路径:一边想要成立与白人社群对立的黑人社群,另一边则要建立基于共享认同的社群,其中的人们拥有共同的目标以及价值观。我倾向的是后一种而非前一种。
界面新闻:但现实中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比如在美国,设想一名黑人与一名白人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二人都是高科技领域的工程师。对此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种抱怨是,数年之后管理层中多半还是白人。如果只把这两个人看成美国人、或者工程师,那可能就没有触及到深层次的问题,种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被忽视了。在性别方面也类似的现象,现有体制下男性经理的数目比女性要多得多。不少论述会认为,识别并承认族裔、性别等身份认同,外加设置某种配额,不失为一种矫正现有问题以及历史不公的方法。
约翰·凯:这里不妨引入一个过渡阶段(intermediate stage)的概念。我们大可以承认,那些曾受到歧视的诸如黑人或是女性之类的群体,在历史上的确可能被禁止担当某些角色,但我认为此类禁区只是暂时的、权宜性的,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亡,人们说到底还是希望仅被当做工程师或经理来看待,而非黑人工程师或是女性经理人。
界面新闻:你写过许多讨论英国政治与经济的著作,这两本书也同样聚焦于一系列英国问题。可否请你谈一谈,对世界上的其它国家而言,它们能够提供怎样的经验教训?
约翰·凯: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课便是:不可让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代理者走向极化。这不仅对英国成立,也普遍地适用于各国。另外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我们不必在个人主义与国家管制之间做简单粗暴、非此即彼的选择,二是要重视社群——尤其是以居住地和工作为基础的社群——在人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
(感谢高铂宁对此文的贡献)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