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从双十一每年交易额都屡创新高到“爆买”一词成为日本人对中国游客的刻板印象,从国货崛起到直播卖货,中国人看似不断增长的强劲消费力成为近些年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屡屡引发热烈讨论。2019年年初,一篇题为《月薪一万却吃不起车厘子》的网文刷屏,“车厘子自由”一时成为城市中产衡量自身消费水平的一个标尺,随后更是出现了一系列的“XX自由”,暗示着中国消费者看似无止尽的消费欲望。但在最近两三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消费的问题正在做出更多的反思。
在今年译介面市的《制造消费者》一书中,法国学者安东尼·加卢佐从18-19世纪商品经济在欧洲的兴起谈起,揭示了世界从农业社会或生产社会转型成为消费社会后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在日前一场新书分享会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评人马凌与上海财经大学讲师梁捷围绕此书,对种种消费迷思展开了讨论。

只有当大众消费者出现,消费社会才宣告成立
根据马凌的观察,关于消费社会的批判理论主要有三派:一派是以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观念为核心的理论,对消费主义持悲观、批判性的态度;另一派的意见更积极正面,从物质文化、文明技术发展的角度指出,人类与消费和商品并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第三个目前正在崛起的流派则聚焦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们通过消费自我赋权、自我表达。她认为,《制造消费者》以凝练的语言将上述许多理论呈现在一本200多页的书中,是她愿意向自己学生推荐的消费社会理论入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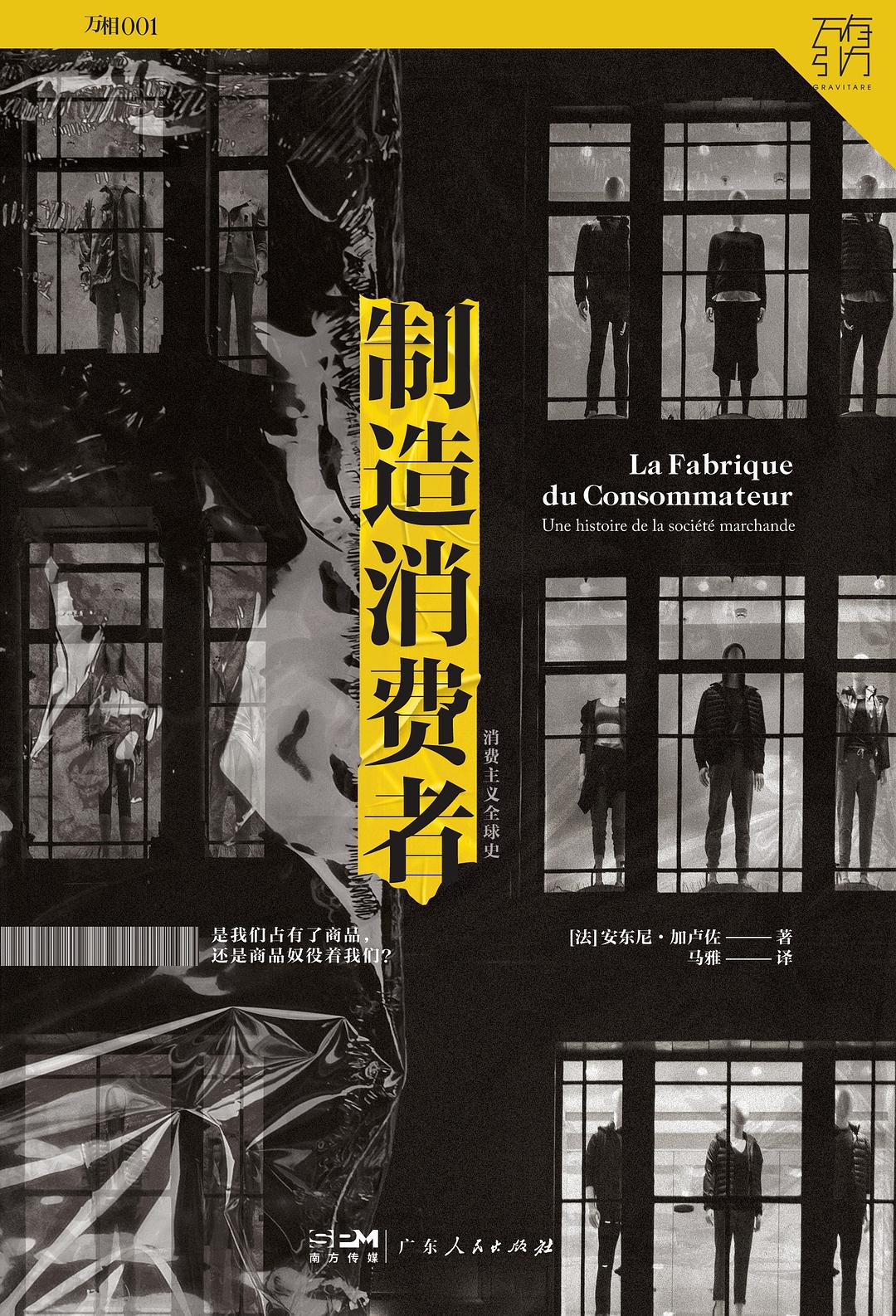
[法]安东尼·加卢佐 著 马雅 译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6
商品、贸易和消费自古有之——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地理大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一个欧洲主导的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研究明代的历史学家也注意到,晚明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期,艺术史学家柯律格就以文徵明曾孙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为例,分析了明代文人所欣赏的器物如何被消费,并且成为文雅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直到19世纪,构成所谓消费社会的种种条件才得以成熟?为什么消费者需要被“制造”出来?

梁捷指出,前消费社会与消费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全球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长期维持在温饱线水平,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从事奢侈品消费的达官贵族,但占社会多数的平民百姓并不是消费者。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世界的面貌因工业革命而发生重大改变——在提高生产效率、掀起供给面革命的同时,也带来了需求面革命。“制造消费者”这一标题精确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即人们开始具有了“消费者”的思维方式,大众消费者出现,进一步沉浸于消费社会,并开始被种种消费符号控制。
马凌提醒读者注意,虽然自社会分工形成以来,商品始终伴随人类同行,但消费社会是一个特指概念,它指的是生产相对过剩、需要鼓励消费以便拉动生产的社会形态。消费社会与此前的生产社会不同,生产社会中的人关注商品的物理特征、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消费社会中的人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和形象价值。
在前消费社会,除了消费者多为上层阶级人士以外,还呈现出一些其他特点。首先是商品文化的地域差异明显,以《长物志》为例,马凌认为,与其说是一本歌颂商品社会的书,不如说是一本批判商品社会的书和明代版本的《格调》——文震亨对当时市面上流行的时髦玩意嗤之以鼻,认为崇古和朴素才是真正文人的追求。
其次,消费的正当性依然在很多地方面临质疑。比如在17世纪因资产阶级革命而高度繁荣的阿姆斯特丹,虽然新兴资产阶级家庭享有中国瓷器、土耳其地毯和意大利柠檬等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品,但正如西蒙·沙玛在《富庶的窘境》一书中所指出的,这种奢侈的物质享受与新教伦理格格不入,因此造成了意识形态层面的矛盾。为此,当时的荷兰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静物画主题“万物虚空”,画面中与全球商品并行出现的是骷髅、苍蝇、蝴蝶或消逝的花朵,以此警示观者财富都是过眼云烟。

女性消费者的行为吸引了不成比例的关注
富人通过炫耀性消费进行阶级区隔的现象历史悠久,但在马凌看来,“没有钱的人消耗奢侈品,这才是消费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就贡献了这样一个案例:爱玛作为一个普通乡镇妇女,受到巴黎时尚杂志的指引进行消费,以至于债台高筑,酿成自杀身亡的悲剧。但需要承认的是,向上攀比的虚荣心是“人之常理”和一种强大的消费驱动力,在历史上,西方社会的种种禁奢令总会因此名存实亡,这其中既有市民阶层对上流社会的钦慕,也有贵族阶层的向下模仿(比如15世纪的威尼斯高级艺伎引领的“恨天高”高跟鞋潮流),“金钱的力量可以冲破贵族等级制度。”
马凌认为,消费社会的分层理论提示我们看到人们在面对炫耀性消费时的微妙心态:“最高的境界是完全不需要攀比,需要攀比和竞争的是中产甚至中产以下的群体,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消费主力大军。和月入20万的人群相比,我认为月入一万的人群可能才是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因此,消费主义批判理论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用消费营造的身份符号来进行身份认同和身份区隔的虚妄。
加卢佐在书中强调了商品作为一种符号对身份形成和界定社会地位的重要性,而广告在打造符号、提升商品吸引力方面厥功至伟。梁捷指出,学界就广告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形成了两派截然对立的看法。其中一派认为广告的目的是促进竞争,不同的商品通过广告介绍给消费者,信息传播得越充分,竞争就越激烈,消费者就能从市场竞争中享受更多好处;另一派则批评广告会抑制竞争。以可口可乐为例,虽然它已是家喻户晓的全球性品牌,依然要在奥运会、世界杯等重大体育赛事上投放大量广告,以此将其他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保持垄断地位。
“现在看起来,广告抑制竞争的特点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的人把注意力作为稀缺资源,尽量垄断。”梁捷自嘲,自己在二十年前阅读鲍德里亚的作品时对他的观点并不是很信服,广告真的有那么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吗?“但现在(他的理论)越来越正确,今天确实是鲍德里亚的时代,广告的注意力控制和符号吸引力在现代经济当中的作用是非常惊人的。”
在讨论消费主义的时候,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女性消费者的行为吸引了不成比例的关注。对许多有性别平等意识的人来说,消费主义鼓励女性关注和投资自己的外表,也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在解放女性的伪装下诞生的陷阱”。马凌表示,女性在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时尚的受害者,而且因为过去女性身份较低,很多时候她们本身就被商品化了。
历史中女性“服美役”(注:一个新的网络用词,指女性为了迎合大众审美和社会对女性外貌的要求,付出大量财力和精力去维护美貌)的例子比比皆是,连女性君主都无法幸免:在以“盈盈一握的蜂腰”为美的时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以自己勒束成14英寸的腰胜过了美第奇家族的一位女士为傲。“如果一个女性国王都无法避免(外貌竞争)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消费时尚对女性的摧残。”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性别解放亦能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19世纪开始,乔治·桑等女性主义先驱打破性别规范的桎梏,开始抽烟、骑马、穿男装,至20世纪初,一批名为“随意女郎”(flappers)的新女性出现了,但她们在不知不觉间也被符号化,成为了新的时尚模特,引领新一轮的女性时尚潮流。“(女性)逃脱消费主义陷阱真的很难,任何有机会的地方都被商品化,资本如影随形。”
梁捷以近两年热议的“海淀妈妈”和“顺义妈妈”为例,分析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加诸于女性身上的无形压力——能把孩子培养成才的“海淀妈妈”尤显不足,既能鸡娃、又能保持优雅气质外表的“顺义妈妈”才更胜一筹。“内卷是看不到头的,卷到最后就是所有人都要试图装出毫不费力的样子,”他说,“对于今天的女性来说,还是要认清楚当中的关键在哪里,再思考自己要选择的方向。”
中国离消费社会还有距离,但反思消费主义正当其时
伦敦大学历史学家弗兰克·特伦特曼在首次出版于2016年的《商品帝国》中提出,90年代中国人的消费水平虽然翻了一番,但储蓄增长了两倍,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是投资而非消费;更重要的是,90年代开始的体制改革让私人家庭需要承担越来越大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成本,这限制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在2006-2016年,家庭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对GDP的贡献从42%降至35%以下,在美国,这一贡献值是中国的两倍,亚洲其他地区的这一比例约为50%。因此特伦特曼认为,中国是精打细算的焦虑消费者,而非消费主义者。

[德]弗兰克·特伦特曼 著 马灿林 桂强 译
后浪 | 九州出版社 2022-8
梁捷指出,消费和储蓄是个人财务安排的两大部分,整个东亚地区呈现出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储蓄率较高。虽然这些年一些令人咋舌的奢侈消费现象引起广泛关注,但整体而言中国人的消费并不高,特别是在电影、戏剧、书籍等文化消费方面,距离消费社会还有较大差距。和消费相比,中国人更偏好储蓄,用储蓄投资的方式进入经济活动。马凌分析认为,英美国家之所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强势进入消费社会,是因为自由主义的体系之上叠加了社会福利,社会安全网络的壮大给了民众消费的底气。而在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福利削减加重了民众在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负担,这必然会对维系“丰裕社会”产生不利影响。这是西方社会给予我们的警示。
马凌认为,虽然中国恐怕还不算是一个消费社会,但反思消费主义正当其时——我们对消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在于,我们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东西?我们要如何应对物质生产和消费过剩导致的环境问题?“西方对于消费社会的反思已经落实到了一些具体的行动上,比如二手商品、共享经济。中国目前可能只有在大城市有这种萌芽,但如果出于环保角度考虑,应该是可行的方向。”她说。
梁捷指出,学界关于环保问题的讨论核心是“贴现率”,即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克制自己的物欲,容忍生活水平的下降,并为此推出相应政策。“这是一个直到现在学术界仍然在讨论的问题,我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呼吁大家关注这个问题。”梁捷表示,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的灾害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保不是一个书面上的或国家领导之间的问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它和其他重要社会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的观点令马凌深有启发,卢卡奇认为,我们应该从对市场的痴迷中获得解放——社会主义经济不是目标,仅仅是人类进化到更新的阶段的前提条件。这一观点的启示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注意,当社会达到一定物质水平后,精神追求是更值得追求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当下在反思消费社会物欲旺盛的同时,也应该注意物质需求之外的精神需求。梁捷发现,如今一些消费者即使是在进行文化消费(比如看展)也是以晒图和炫耀为主要目的,“这种炫耀性消费不具有生产性,你自己也没有真正感到愉悦。如果我们能够减少这些炫耀性消费,真正投入到文化性消费中,不管对于个人还是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作为消费者,可能理念的变化还是应该有的。我们当代的一个问题不是选择不够多,而是选择太多了,导致我们眼花缭乱。人总在禁欲和纵欲之间来回摇摆,在中间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是最好的。”马凌说。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