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中式养生首先做到哪一点?莫生气。2000年初,学者冯珠娣与张其成在采访北京养生者时发现,养生者频繁提到的一条健康忠告就是别生气。“别生气”有很多内涵,可以体现为平衡甘苦、规划起居、尽量控制情绪以及保持良好的心态。
养生者相信,生气会搅乱气息,耗散精气,不利于病情康复,因此应当合理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人们难道可以对自己的怒气收放自如吗?这令研究者感到困惑。养生者确实体现了别生气的智慧。一位六十岁的女性曾多年照料因工伤偏瘫的丈夫,现如今每个月靠着两个儿子的赡养费生活,还不幸患有尿毒症。她认为,养生就是不要做不快乐的事情,干活不要太累,这样对身体和心灵都好。一位刚从工厂工会退休的老工人对养生的理解是吃得多、睡得香,精神饱满。他的人生观相当乐观上进,尤其喜欢用伟人的人生起落故事来开导别人,称自己的一个特点是不生气,就算几个人围着骂他,一般也不会生气,但生起气来就一定要发泄,发泄完了就没事了。
正如受访养生者体悟的那般,莫生气的要诀在于保持平和,而平和就需要降低世俗生活的欲望,同时减少利己的想法。莫生气指向了养生的实质:养生属于日常生活经验,关心的是稳定而单纯的小康生活,只致力于塑造幸福生活,并不深究生与死的奥义,而幸福生活的要义就是找到快乐,不要沉溺于衰老疾病死亡等负面因素。只要能够找到乐子、使人们保持良好心态的活动,都可以算是养生,公园做操、书法、扇子舞、广场舞甚至学英语,都是养生。

为什么需要强调保持良好心态?现实背景在于,人们改变现状能力的确有限。一位养生者过去是一名会计,四十几岁就因病早退,曾患有哮喘、心脏病多种慢性病。她与丈夫、儿子居住在狭小的家中,每天晚上都出门去跳两个小时广场舞。跳舞不仅帮助儿子获得安静的学习环境,还使她感受到了互相关心的愉快的集体氛围,暂时从住房和收入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以养生来绕过生活中的诸种限制阻碍、恢复生命力,这是一种具有韧性的体现。通过养生,人们找到了生命中的快乐,也追寻到了活着的意义,这个意义具体包含什么也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为我” :中式养生思想根基

别生气或者说乐观自足的传统从何而来?《万物·生命》一书以平衡甘苦、追求和谐的理论作为解释,并未指出其思想的根基。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道家的传统思想找寻。冯友兰认为道家思想的中心在于“为我”,“为我”即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可对于什么是自己的利益,道家又分为几个派别:第一派赞成最大程度上的自我保全,适当节制欲望,杨朱思想即是如此;第二派讲究欲望满足而非延长生命,人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是为了享受而生存,应当顺从自然与万物,而非与之对抗;第三派讲究专靠节制不行,还须有修养和避害的方法;还有一派认为需要了解天道和人道,按照规律行事可以避害,老子的思想就是如此;最后一派认为灾害是偶发的,了解规律也不能避免,最好就是忘我,这是庄子的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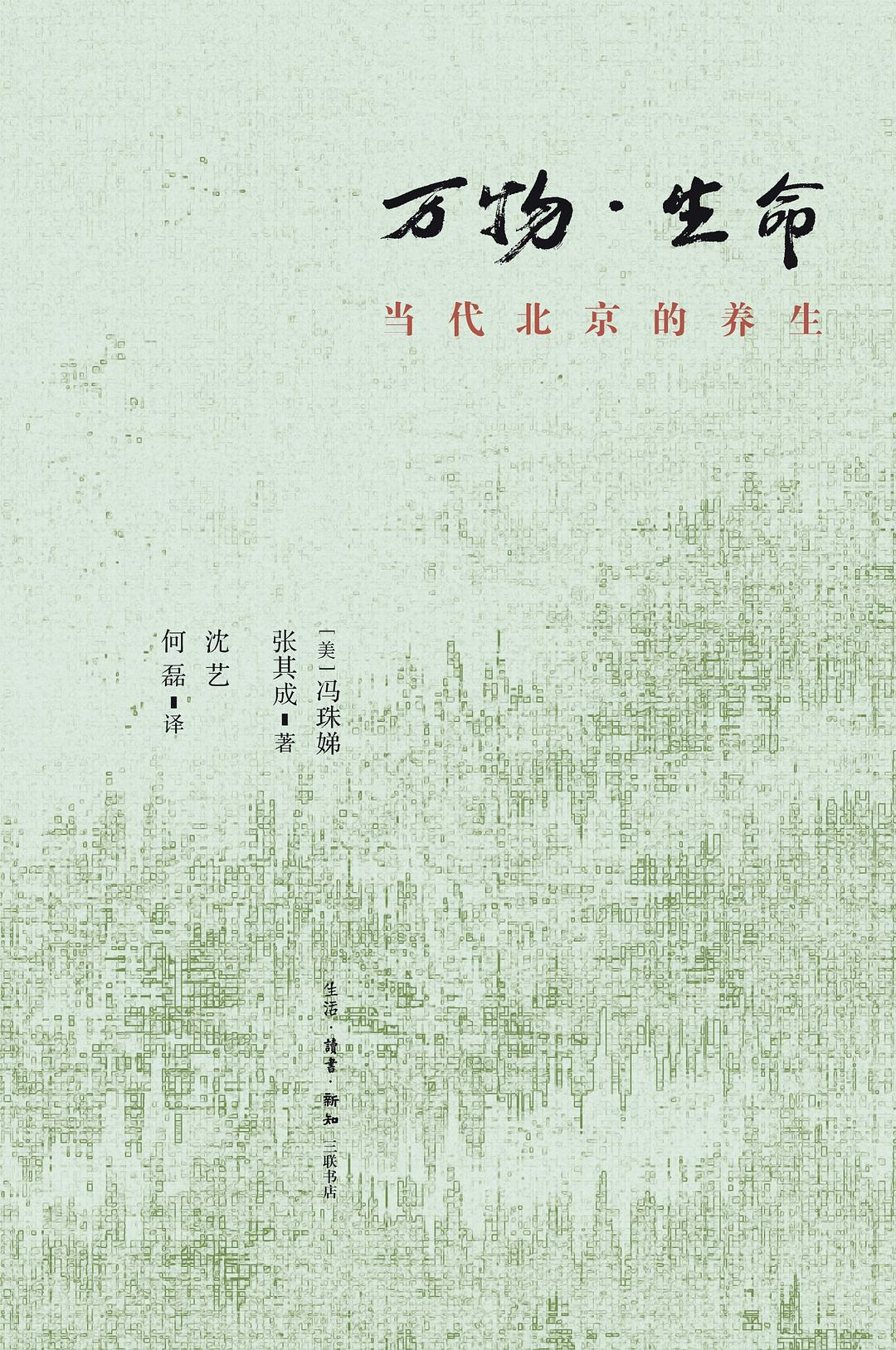
[美]冯珠娣 张其成 著 沈艺 何磊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4
这几派或是赞同全生,或是享乐,或是延寿及避害,只有庄子提倡忘我。其中,对我们今天讨论养生最有借鉴意义的,就属第一派即杨朱的“为我”及“贵生”思想。学者颜世安在《庄子评传》中评述道,杨朱派的“为我”影响甚大,是战国隐者文化发展状态的特征,当时隐逸与有隐逸倾向的人已相当多。自我保全一方面的确有与黑暗抗争、追求个人洁净的意义。隐者的“为我”与世俗的“为我”有极大区别——世俗的“为我”是为了攫取占有更多稀缺资源,诸如功名利禄;而隐者的“为我”,是将未被占有欲望伤害的原始真我解救出来。
然而,对“为我”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演化成对肉体不朽的执着,具有向现实妥协的意思。隐者相信,生命的意义虽然与现实社会的功名利禄无关,却与其背后的更高的神秘安排契合,所以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可以安放个体生命,“杨朱派竭力保护不为外部诱惑所动的自我,实际上不知不觉之中是在追求由日常小愉悦构成的稳定安宁的生活。”颜世安写,这种对安宁生活、日常小愉悦的追求,实际上包藏着顽固的平庸,养生长此以往也演变成了一种类似崇拜肉体长存的自我拜物教。

颜世安 著
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2-10
杨朱派的养生主张日常生活欲望得到满足,对世俗生活寄予厚望,在战乱世道中尤其能俘获人心。仔细分辨起来,不为外部诱惑所动的自我,不正是“别生气”的主体?退休老工人所体悟的养生就是吃饱睡好养足精神,退休老教授总结的以不争来保持平和宽容待人,都像是杨朱派“为我”的当代表达。“为我”让人们较为宽容地看待外部困境,所谓收入、地位、顺逆境遇都是外物,人应当更多地回到自我之中来,虽然有安于现状妥协的一面,但也为真实新鲜生命的存在拓宽了空间。
《列子·杨朱》就借助养生批判了一些主流的想法,与以养生批评世间不和谐现象的养生者颇为相似,如小人殉利是不可取的,君子殉名同样不见得高明;人们需要在贫困与劳累中谋得平衡,因为过度劳累是累身的,而长期贫穷亦损于生机。这种微妙的、动态的平衡心态被今天的养生者分享,也是令研究者感到惊讶的养生心态富有韧性的体现。
未敢忘忧国:养生的心灵作用
虽然从“为我”的思想出发,六欲皆得所宜事实上并非只是为了驱壳,养生的乐趣是养生者愿意不断讲述的。比如对那位因病早退的会计而言,广场舞成为了她参与集体生活的纽带,能够在舞蹈中感受到互相关心的快乐。养生养的不单是身躯,也回应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不管这些意义是什么层面的,总归是被养生者理解并且认同的。一位工作压力大、经常吃垃圾食品的警察将养生之道与提升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结合起来,也将养生视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跟预防疾病和延年益寿相比,养生最主要的意义是提升心灵。上文提到的那位退休的教授也坚信,锻炼思想才是养生的核心,他将思想总结为有正确的三观,服务社会和国家。
养生有助于提升心灵,锻炼思想也能更好的养生,《万物·生命》一书注意到,中国当代养生者表达出来的社会公共意识与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有关,但也许没那么直截了当。在石一枫的小说《心灵外史》里,大姨妈为了提升“我”的健康和智力,带“我”去密林深处练功,用掐树的方法聚气发功,再用发功的手猛拍在孩子的天灵盖,用自然的能量将身体里的坏能量逼出来。她从师父那里听来,气不仅关系着小孩子的体力和智力,还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以及宇宙的奥秘,国家和宇宙都是由好能量与坏能量交替支配的。作者以调侃的笔触写出了不识几个字的大姨妈对神秘力量的轻信与执迷,以及她从儿童发育联系到宇宙运转的胸怀与想象力,“一个县城妇女,除了做饭并无一技之长的食堂职工,居然谈论起了民族复兴、世界和平。什么叫做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就叫位卑未敢忘忧国。”大姨妈不仅用“气”指导生活获得好处,为外甥创造更好的前途,也在心灵上甘愿受“气”的指导,她相信能量就是事态的成因,气就是事物运转的最终答案。她教诲外甥:“万事万物除了他表面的形态以外,都带着一股无形无迹,连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出来的能量。”
问题不在于为什么大姨妈会相信这种粗制滥造的理论——即便用了很多夸张的描述,作者对大姨妈的态度明显同情大过嘲讽——而是为什么大姨妈不满足于“科学仪器”以及“表面的形态”。她需要“气”和“能量”,不仅因为她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需要一个简明实惠的解法(大姨妈患有不孕症,她期待神功能使她怀孕),更因为她需要某样她也不了解的东西来填充心灵。用小说的语言就是,如果知识分子能用理论炸药填满自己,大姨就是在不断地寻找能填充心灵的其他材料,她的毛病不是别的,就是不甘于心是空的。她想要相信什么,因为一旦相信了,她就能摆脱生活里的所有苦。在气功大师那里她找到了“灵魂的共振”。大姨带着“我”怀着朝圣的心情前往神功宣讲的会场,在那里“我”看到了人生中最迷幻的现场表演之一,看来像大姨妈这样急于填满空心的人数以千计:“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都被牢牢地摄住了,定住了,控制住了……你能想象上千个灵魂集体性地、以高度一致的频率共振,是怎样一个场面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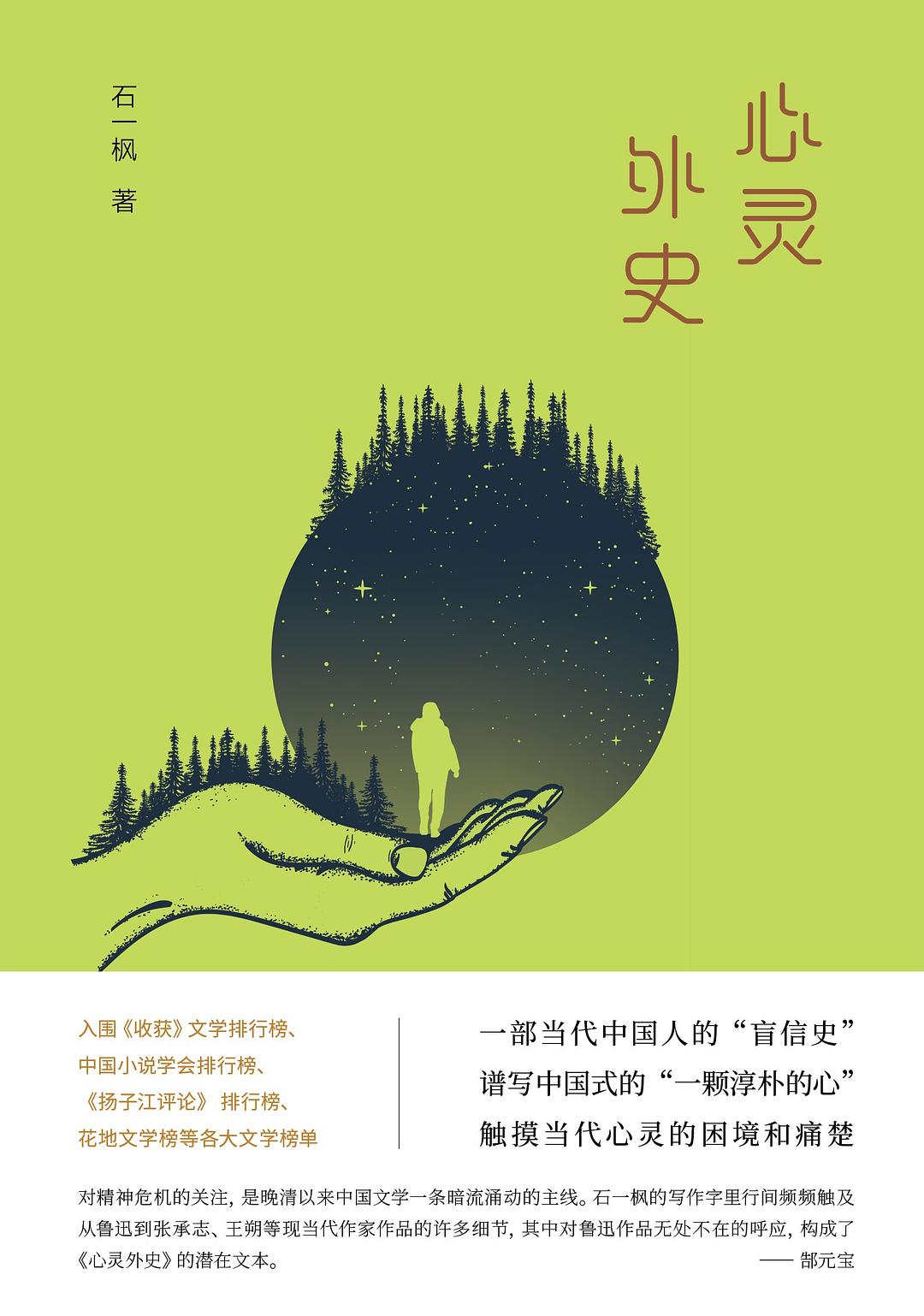
石一枫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9
养生者通过养生获得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既是具体的,就像退休会计通过广场舞认识了更多人,感受到了集体的关心与快乐,同时也是抽象的,大姨以“气”和“能量”将自我与更大的世界、社会、国家乃至宇宙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能是基于想象的,或者是不经反思的,可疑又粗拙,但确实能如岸边的锚一样固定住他们漂泊悬浮、饱受磨难不知如何安放的心灵。
虽然这一点经常不被本人察觉,养生的功效也经常被不假思索地表达为类似城市宣传标语或者健康宣讲口号的语言,很多养生者都同意养生就是为社会做贡献,还会将内心需求简化为与躯体健康相应的心理健康,将养生的意义朴素地描述为“以后能越过越好”。但是,这种混同和简化也可看作是一种挪用,人们挪用最唾手可得的理念,不太准确地传达了对安抚心灵的渴求。小说里的大姨妈和采访里的年轻警察都相信,通过气的运用,他们可以透出纷繁世界的谜底更好地活下去。这是人在面对变革时的正常反应,近代知识分子面对先进的西洋技术时,也曾想象过引进电气磁力等技术铸造强健的国魂国脑,这是一种强烈意愿的表现。
健康乌托邦:生命本身是最高的善?
值得补充的是,中国传统里也有与贵生重己的养生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列子·杨朱》讲述认识到与其贵生爱身还不如顺从天命,因为无论怎么爱惜生命和身体,还是会走向死亡。庄子认为,生命的形体与生命本身具有区别,养形不足以存生。如颜世安解读的那样,归根到底,个人并不能安顿在温和稳定的小日子之中,人类存身的宇宙也不会善意地保护这种安稳的意愿。后世晋代诗人陶渊明在诗中表达,人们养足身体是为了全此一生,可是一生就像闪电一样短暂,浮生如梦幻之中,死时还是一切成空,“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能复几,倏如流电惊。”在这里,不仅功名利禄不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侍奉身体与延长生命也不那么重要了,因为生命亦要随自然而化,所以人最终的结局就是托体同山阿。
法国人类学家迪杰·法桑的著作《生命使用手册》对健康在当代社会的至关重要性提出了质疑。人们不再去问什么是善和好的人生,生命本身就构成了最高的善,任何行动都可以以此为名义来合法化自身。难道生仅仅是死的对面吗?仅仅作为死的对面的生,还算真正的生命吗?作者引用本雅明与阿伦特的观点表达将生命化约为物理存在的现象。在《暴力批判》一文中,本雅明写道:所谓活着比正当地活着更优先是错误和可耻的说法,如果活着只意味着生命的存续而已。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谴责,现代社会政治上最有害的一种教义,亦即生命本身就是最高的善,以及社会中的生命过程应该占据人类一切奋斗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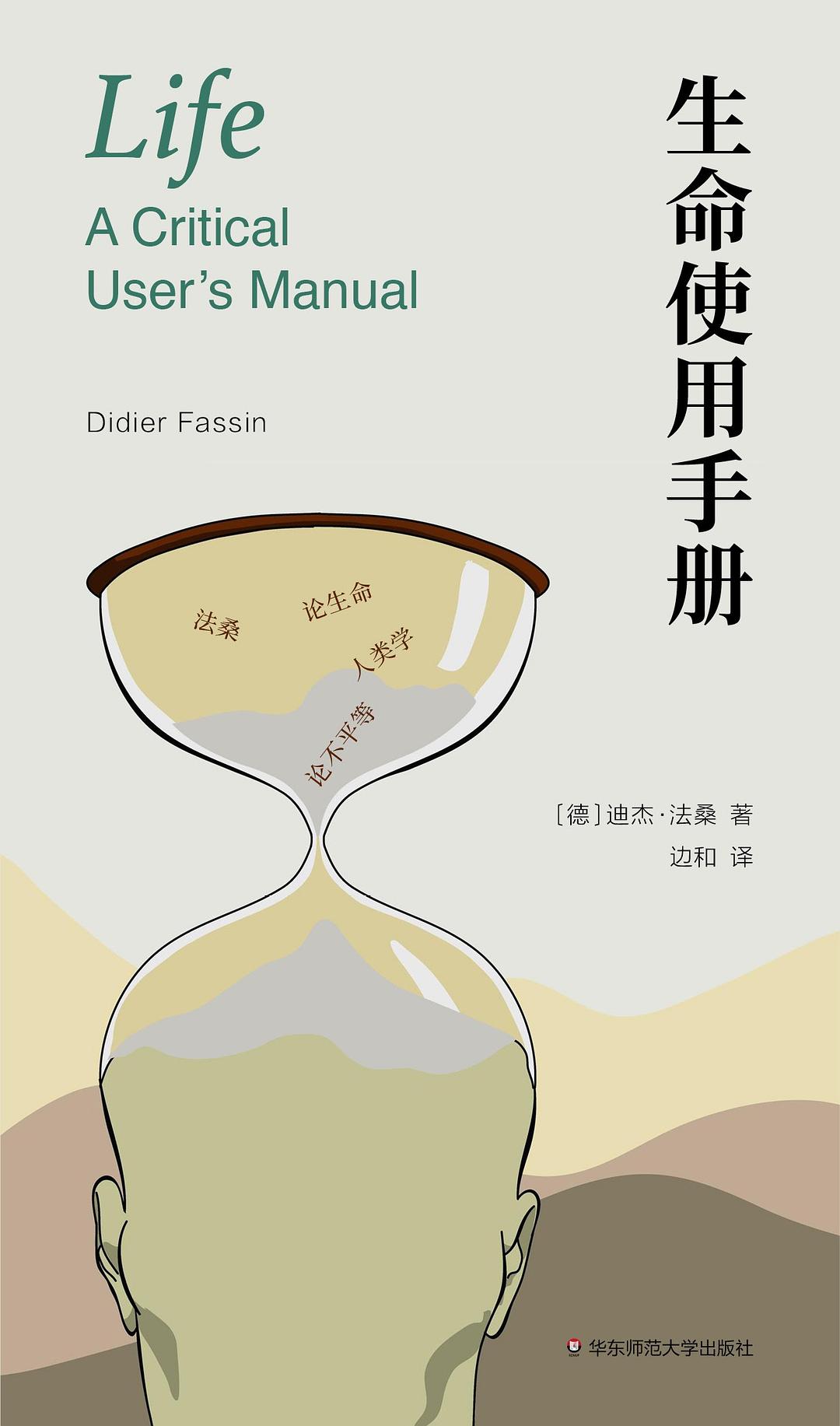
[法]迪杰·法桑 著 边和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4
生命本身是最高的善的思想并不只是现代社会政治的教义,我们在托马斯·莫尔创作于16世纪初的《乌托邦》中就能找到原型。乌托邦人怀有非常清新的价值观,他们无视财富珍宝,全民务农为生,按照集体的节奏生活工作与娱乐,安稳有序地在各自的城市居住,前往他地需要得到文件准许。乌托邦人将按照自然的指示生活视为最高要求,将身体健康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他们视健康为最大的美德,亦是所有快乐的基础和根本——只要有健康,生活就安静舒适;失去健康,就绝对谈不上有快乐的余地。没有健康而不觉得痛苦,乌托邦人认为这是麻木不仁而非快乐。
乌托邦的优越,不仅在于世界上粮产丰富、牲畜兴旺,也在于人民体格健壮、甚少生病,或者说两者根本就是一回事,因为都是实惠有利的。乌托邦人以此为标准衡量其他事物,他们在意身体健壮,热爱可口的饮食,因为能够令人们健康受益;也最重视医学这门学问,因为医学最有利于维护身体健康。与此思路一致,乌托邦人认为改造自然环境很有正当性,因为只要人们能够从其中受到实在的好处,就算天翻地覆也是非常正面的。于是人们看到一整座树林被人用手连根拔出从甲地移植乙地,这不是为了繁殖树木,单纯因为乙地近海便于运输。
《乌托邦》是善与健康维护得很好的理想国度,小说《南十字星共和国》则是它的反面,讲述了一个基本构造和乌托邦一模一样的地方——一个本来团结有序的工业理性王国,人们集体工作生活,保持严格的作息,接受完善的公共福利与医疗保障——在遭遇瘟疫席卷时,文明是如何土崩瓦解的。健康这种至高无上的善在遭遇灭顶之灾时,人们变成了在原始的土地上流浪的野兽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