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期主持人 | 林子人
前两天我读了一篇题为《刷完上千本海外言情,我总结了全球女性的情爱幻想》的文章。作者在一家海外网文公司做了一年多有声书编辑,她在文中分析了全球网络文学中言情小说的趋势,与中文言情既相似又有差异,特别有趣。最让我惊讶的是这一个发现:中西方网文都在呈现保守化趋势,比如强调女性贞洁,包办、契约婚姻或强制爱剧情频繁出现,但有意思的是,喜欢保守化题材的女性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就是求爱不得,渴望被支配的弱女子,相反,很多人其实不缺爱,而且是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
这周上海在演的一部话剧《女权主义者恋爱手册》则用一种更“极端”和幽默的方式展示了上述现象。剧中的男女主角是一对情侣,特别的是,男生的性别意识比女性更“进步”,时刻尊重女性的意愿和选择,但在女生看来,会“壁咚”的男人比自己那总要问“我是否可以”的男友可性感多了。这部剧改编自英国剧作家、记者和评论作家Samatha Ellis的《How to Date a Feminist》,在写出这个剧本之前,Ellis还出版过一部回忆录《如何成为女主角》(How To Be a Heroine),在书中回忆了自己作为《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等浪漫小说读者的经历。Ellis显然把自己的经验诙谐地放进了剧里——女主角的理想型是《呼啸山庄》中的希斯克利夫,对爱情有许多被浪漫小说形塑的粉红色幻想。
坦白说,我在少女时代没少看言情,现在这也是我的guilty pleasure。但我很清楚,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是不同的——经历和学识已经武装起了我的大脑,让我能够用女性主义的批判眼光去看言情。去年读《暮光之城》的最新续篇《午夜阳光》,我发现了曾经作为狂热读者的自己没能发现的问题:此类异性恋浪漫小说在如何挣脱关系式命运的束缚,设想一个女性能够获得真正独立、自由和尊重的未来方面,不能给予女性读者任何参考;美国学者珍妮斯·A. 拉德威(Janice A. Radway)于1980年代在《阅读浪漫小说》中提出的论述,至今依然能有效地用来解读言情题材的范式和它对女性读者的吸引力。
于我而言,我的困惑因此是,喜欢言情就显得不够“觉醒”吗?如果说爱情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概念——言情等流行文化显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的情感体验和对浪漫爱的想象是否能跟上我们的观念变化?言情对女性持久的吸引力究竟源自何处?对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借此次聊天室的机会,希望听一听各位的见解。
01 没有沉迷过通俗言情,恐怕也难以领会正典

董子琪:请问子人最近在读什么言情?能感觉到你对言情题的强烈关注,能不能简单举几个例子,特别想知道。
林子人:小说倒是没有,今年大火的电视剧《梦华录》和《苍兰诀》都看了(笑)。还看了《罗莎琳》(Rosaline),一部以罗密欧前女友的视角重讲《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的浪漫喜剧电影,女主人设还挺有现代女性意识的,所以就挺好玩。
对了,追剧期间我还在Lofter上潜水看同人文,注意到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就是异性恋CP的同人文中“怀孕”是一个很常见的梗,基本上行文逻辑就是女主发现自己怀孕了,男主既高兴又忐忑,加倍疼惜女主。我认为这与当下年轻女性的婚恋特别是生育焦虑息息相关——在幻想中的亲密关系里,女性在生育中的巨大付出不仅能得到爱人的承认,而且能被珍视和补偿,而且孩子的到来不会损失恋爱的甜蜜。
我对言情题格外关注,主要是因为我没想到都2022年了我还会津津有味地看一部仙侠剧,而且觉得特别治愈。在外部世界格外动荡的当下,我突然理解了仙侠为什么会是一个常青题材:仙界的人动辄有几万年的岁数,即使死亡也能不断转世重生,这就意味着仙侠故事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困境和痛苦,在这个基础之上,生生世世的爱情增添了生活的情趣。我确实在今年感受到了言情具备的逃避现实的力量。

不过,今年我也尤为强烈地感受到,言情是一种特别“岁月静好”的故事类型——生活顺风顺水的时候,“充满激情的爱情”尤其容易被认为是生活中最激动人心、最有反叛意味的东西,忽视所处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对人的异化,进而可能对亲密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现实生活已经像一部卡夫卡小说的时候,言情是能带我们逃避现实,但它的平淡庸常也难以掩饰。我觉得这可能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读者有些羞于承认自己会看言情,觉得它难登大雅之堂的根本原因。
尹清露:我没看过太多言情小说,但看过很多纯爱漫画/电影,它们往往不避讳现实残酷、着力描写女性勇敢的一面,也许可算是“女性主义言情”吧。矢泽爱的《天堂之吻》讲的就是一个颇有才华却局促的少女突然闯进绚烂的时装界、遇见绚烂的恋人的故事,只不过女主没有等待爱从天而降,而是会在爱中思考和行动,或者即使走得慢一点也在逐步前行。前两年的纯爱番《恋如雨止》讲述了美少女爱上年上大叔的故事,她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各种打直球——写情书、当众表白,虽然大叔无法回应少女的心情,但是当“爱情雨过天晴”,两人都有被拯救、焕然一新之感。所以,我看《苍兰诀》时觉得甜蜜、毫无违和感,也是觉得两者的关系平等,有成长也有较量,而非一方俯视一方承恩,也非人们现今热衷的“欲擒故纵拿捏术”。
董子琪:我一直觉得女主角是女性主义者才吸引人呢。九十年代到2000年我看过很多言情电视剧,应该是电视上播什么就看什么,主要有琼瑶的“梅花三弄”、《新白娘子传奇》、《青河绝恋》还有《情深深雨濛濛》。在《情深深》还没有成为显学时,我就疯狂着迷,还找到了小说《烟雨蒙蒙》来看,吸引我的是女主陆依萍的特质个性独立、爱恨鲜明、富有才华又命途多舛,这都足以激励我。女主被深刻地爱着,这是她素质、才华、人格各方面优于他人的证明,陆依萍的何书桓可不就是她卓然超群的展现吗?从这个角度说,不管她是不是复仇,男主确实是她的战利品。后来才看到琼瑶说写这部小说时脑海中的模本是《呼啸山庄》,她在26岁时想写一部爱情复仇故事,所以就成了这部小说。所以我是先看的电视剧,再看的原著小说,接着才看的《呼啸山庄》。这是一个由产业下游向上再向上的过程。

到很后来我才关注起通俗言情和纯文学之间的区别,我感受到十几岁时看琼瑶轻易燃烧的火焰、喷薄欲出的泪水、顾影自怜代入的模式随着时间流逝而失效了,也觉得简·奥斯丁笔下的人物与故事确实是更值得推敲的,如果有人说简·奥斯丁写的不过是玛丽苏小说,这是值得为之争辩的。可能是有距离的感情,有节制的表达,更包罗万象的布置以及不希望以情来摧毁一切经验和规矩?
琼瑶受《呼啸山庄》启发书写《烟雨蒙蒙》,确实也提示了我们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正典与流俗之间的微妙距离。你看到的电视剧或许是对某部正典的模仿(也许是自认为的),而正典更可能是建立在这些通俗作品之上的血肉相连但又品格不同的“近亲”。这种区分的意识是如此地强烈,《诺桑觉寺》安排女主热爱阅读类型小说,又让她怀揣着不切实际的想法闹了大笑话,《红楼梦》里贾母也批评才子佳人小说闹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都是一种有趣的互文。可是如果我之前没有看过那么多言情电视剧,听到过无数振聋发聩的“吟霜”以及因不可遏制的激情破坏的家庭,可能也无法领会这种从成熟立场的回顾与讽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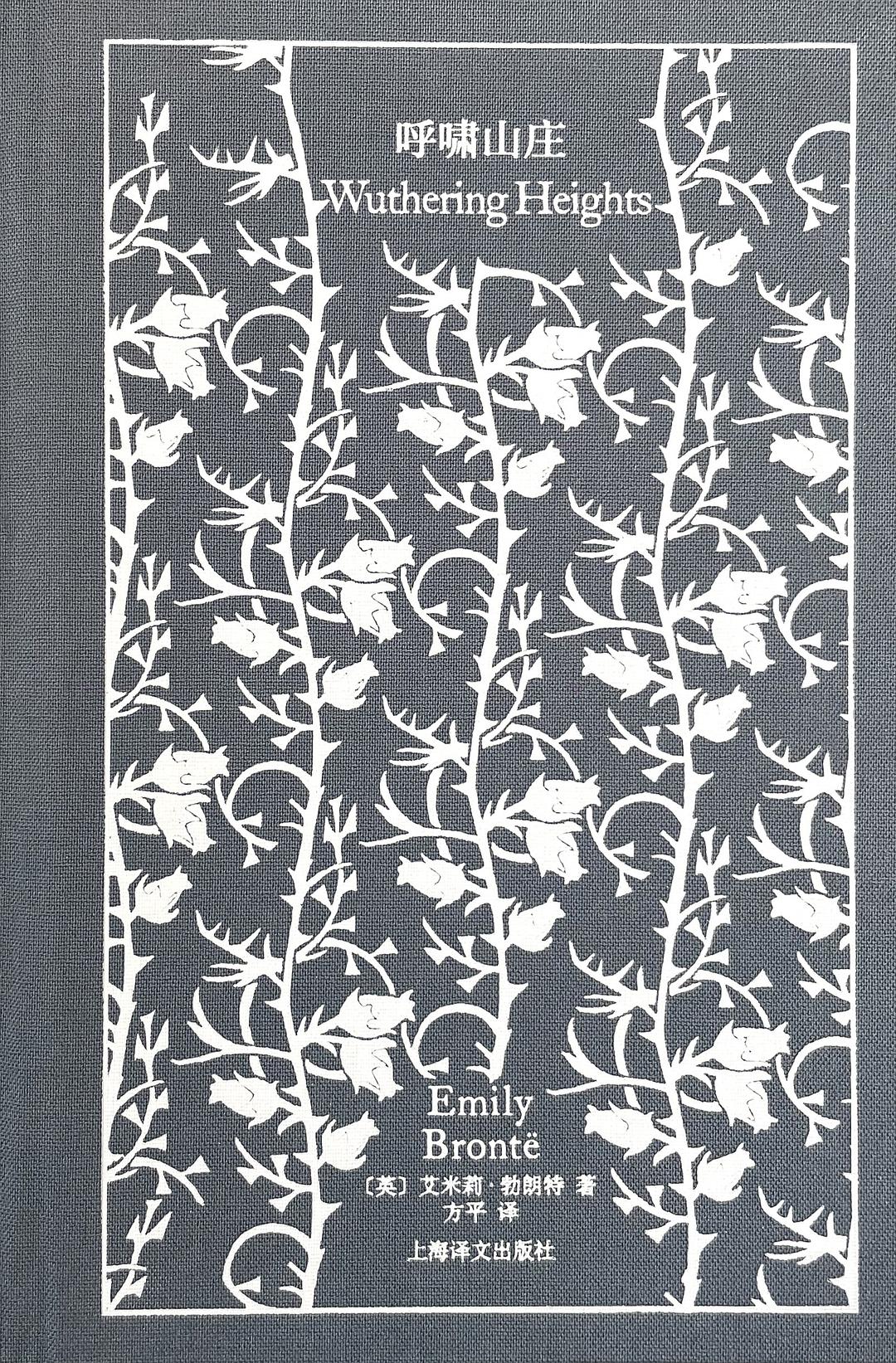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方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
对于读者,“包法利夫人阅读综合征”是经常被提到的一个词,批评者认为有些热爱阅读尤其是言情的女人将阅读等同于吃食,无法体会满足欲望之外的审美作用。这类批评应该对准千篇一律的套路和类型文学过于产业化而非某类读者。这大概是一种担心,如果一直被喂糖霜,味觉可能会被破坏掉,以至于无法体会更丰富细微的感觉。套路是容易识别的,“真情”却容易让人蒙蔽,言情小说的故事模式更是吸引人,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追寻真爱的人陷入杀猪盘了。
02 女性主义者和言情爱好者之间当然有冲突,它让我们更理解父权和女性主义
潘文捷:子人问如果喜欢言情是不是就显得不够“觉醒”,能理解这份困惑。确实,女性主义还在追求一种理想——2022年度《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说男女平等还要132年,喜欢看言情却是生活的现实情况导致的结果。此前已经探讨过霸总为什么流行,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更倾向于男性群体,更多的资源往往都被分配给了“成功人士”,女性通过男人才更能实现自身的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甜宠等言情的流行也与如今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密不可分。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谈到过,今天的人处于孤独之中,人为了消除孤独,宁愿不要自由。久而久之,人在无意识中形成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怎么才能达到逃避自由的目的呢?一种人选择控制他人,而另一种人希望让自己被他人统治、保护和控制。他们本质上都不自由,区别只在于把自己交给他人还是让自己统治他人。如果说“霸总”属于那种统治他人的人的话,很多人喜欢这种角色,当然是因为自己内心有把控制权交给他人的一面。
现实生活要支棱起来已经那么累了,看电视剧看书还不能懒惰一下吗!如果你打开最近频上热搜的《点燃我,温暖你》原著《打火机与公主裙》的页面,就可以看到本书的简介是这样的:“我有我的国王,我是他的不二之臣,我愿为他摇旗呐喊,也愿为他战死沙场。”这就是女主的独白,好家伙,你的人生都寄托在他身上了,那你自己的人生规划在哪里呢?当然了,为自己打拼是很累的,寄托在别人(包括配偶、子女、偶像等)身上不就啥也不要做还与有荣焉了吗!
有趣的是,不仅女性有这样的心理,男人也是啊。在备受诟病的《东八区的先生们》里,虽然张翰的角色是一个喜欢控制他人的国产霸总,但男四号向小飞向我们展示了男性内心的另一面。他喜欢身价上百亿而且对他管教严格的御姐刘胜男,认为她可以让他少奋斗十年,近几年比较火的“阿姨我不想努力了”的梗也与之类似呢。
尹清露:虽然如文捷所说,男性占据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女性正因为得不到又想要得到才导致了对霸总的迷恋,所以也如《始于极限》中铃木凉美担忧的那样,女性主义的主张明明是“不需要男性也能做好自己”,对男性的认可欲求却戳破了这个主张。
另一方面,上野千鹤子的回应是——“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回报不来自他人,而来自我们自己。”东方青苍心思细腻却在情感方面十分匮乏,小兰花刚好能教会他怎样去爱,她让东方青苍第一次感受到无条件的友善,会妥帖又随意地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厨房里有晚饭你自己去拿吧”,而这是因为她有充沛的爱所以不吝啬拿来分享,我觉得这是非常女性主义的部分。同时,东方青苍学会了关爱别人,小兰花也受到对方坚韧品格的影响,“神女”的设定虽然未免流俗,但也说明小兰花开始变得羽翼丰满,这个过程并不属于“女人有了事业才有实力恋爱”的割裂话语,而正是在爱中发生的——当小兰花成为强大的神女,她的神态和当初的东方青苍又多么相似。

[日]上野千鹤子 [日]铃木凉美 著 曹逸冰 译
新经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 2022-9
日语里有“男要勇,女要娇”的说法,女性主义言情故事可以把它倒置过来——变成“男要娇,女要勇”,我不觉得这在现实中无法达成,即使这样的关系远非主流,并且绝大多数仍是女性被“霸总”吸血和利用居多,使得女性必须时刻提防、根本拿不出多余的爱。但是达不到并不说明这种爱不值得被欲求,这可能也是我们会被言情小说或纯爱故事持续吸引的原因。
徐鲁青:言情小说里除了霸总和傻白甜女主的经典模式,还有另一种流行故事类型,如果忽略子琪提到的正典与流俗之别,我会把它们称为“简·爱式言情小说”。这类小说强调男女主角的精神平等,女主独立自主,有自强自尊的性格与独到深刻的思想——书里常常暗示,正是这点让她区别于大多数女性——而男主则是能发现并欣赏她的才华与内心的人。常与之搭配出现的是灵魂伴侣(soulmate)式叙事,很多针对女性受众的言情电影不断强调“爱人是我的另一半”或“灵魂伴侣”的存在,我看的第一部韩剧《大长今》就属于这个类型。
然而仔细想想,亲密关系里的伴侣是精神交流最重要的对象,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理所当然。最近读的《消解单配偶制》(Undoing Monogamy:The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Biology)里提到,大多数女性都默认异性恋排他的性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比友谊更重要),soulmates则一定是排他关系里的伴侣,社会文化在 “与性有关的爱”和“与性无关的爱”之间建构出了高低差序,亲密联结的“终极形式”通向的是 “与性有关的爱”。这当然是言情故事里不容置疑的一点,如果soulmates最后“只能”成为朋友,观众是会摇头流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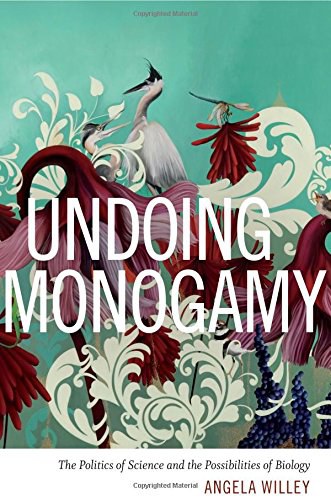
Angela Willey 2016
这些叙事的可疑之处没有霸总那么显见,却始终影响着我对关系的理解,限制我创造更有想象力的、自由深刻的情感联结。然而在挣扎里我也知晓了局限之网的形状,在与成见较量中理解曾被影响过的自我与情感,也在试图挣脱定义边界时更加懂得自身和关系里的对方。女性主义者和言情爱好者之间当然有冲突,但它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更像一场竞技比赛,在交手里我更明白了父权是什么也更理解了女性主义。
03 耽美小说既可以安放女性的浪漫爱想象,也可以探讨边缘群体的困境
林子人:《刷完上千本海外言情》那篇文章里还提到,中西方言情的差异体现在BL(男同言情)题材在中国的异常火爆上。之前我采访学者倪湛舸时聊到了这个问题,她的观察是,目前的很多言情小说其实对浪漫爱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了——传统异性恋言情中恋爱的比重越来越少——仍然在“言情”的那些网文就会跳出既有的性别规范,把对浪漫爱的想象投射到一种幻想性的关系(fantanstic relationship)里,只有在那里才会放心大胆地做浪漫想象,这个姿态本身具有一定的反叛性。
叶青:耽美小说会是一个出路吗?诚然,很多耽美作品依然符合传统异性恋言情故事的套路,只不过男强女弱变成了攻强受弱,若是把角色之一的性别换成女性,其实毫不违和,角色的动机和性格依然限制在一个非常老旧的且由强势角色主导的异性恋框架中。但越来越多的耽美创作者在试图跳出这个框架,像是清露提到的“男要娇,女要勇”,耽美小说中就有诸如“哭包攻、少女攻”之类的人设,打破了传统的“强弱设定”,但我认为这主要归功于网络文学的多元性,载体倒不一定非是耽美小说。
同时我还发现,不少欧美耽美小说不再光是谈情说爱,更多的是专注主角的个人探索与成长,说是青少年文学可能更为恰当。比如前段时间很火的《Bully King》里,主角Jonah和Roman之间的感情纠葛,其实服务的是二人对身份认同的构建。相遇之后,出生于宗教家庭Jonah开始正视自己的欲望,不再被神父父亲压抑和束缚;Roman也意识到了自己内化的恐同,并选择站出来抵抗家暴成性的父亲。今年年初开播、改编自同名图像小说的《心跳漏一拍》,则更关注酷儿群体日常的困境与烦恼,像是厌食、霸凌、抑郁症等等。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