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商韬略
据媒体消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黄达,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18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相比今天的明星级专家、学者,黄达教授显得有些默默无闻,但他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金融的学术与理论贡献却是功不可没。
黄达教授是“中国货币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中国金融学的奠基人”。2007年,华商韬略出版《华人金融家》时,曾有幸采写黄达教授,现摘编部分内容,敬表追思。

黄达,1925年2月22日生于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回忆少时经历,黄达对自己在天津第一中学的高中学习尤其印象深刻。“这所学校只招男生,入校后一律剃光头,常被戏称为‘和尚学校’。学校纪律严明,教学堪称一流。”
在那里,黄达遇到了裴学海、杨学涵、王荫浓等多位顶尖老师,而且兴趣广泛,博览群书,但高三那年,一场伤寒病叠加战乱的艰难,使他失去升学的机会,中止了学业。
此后,原本希望像父亲一样学工并且做工程师的黄达,先后在旧政府机关当过小职员,在私人照相馆当过帮工,在亲戚家寄生“蹭过饭”,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春,才再考入了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财经系,并且在年底就“晋级”为了政治学院的研究生。
但这个所谓的财经系,学的基本上只有两样:一是革命理论、一是参加土改运动,研究生,研究的也不是经济,而是“边政建设”(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
因为学的主要是“革命”,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中(1946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后来回忆起这段岁月,黄达更愿意将其说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7年,刚刚“晋级”为研究生,22岁的黄达又被再次“晋级”了:被学校分配到校部从事行政工作,先后担任过班主任、区队助理等职务。
1950年,经党中央和政务院批准,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当年秋天,黄达成为人民大学的第一批教员,被分配进了学校财政系一个专门讲授货币银行学科的教研室,它当时有一个长长的名字——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
这下可是要来真的了,而且肩负的是,为新生的共和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财政金融学科体系的使命。没有真正学过财经,却要真正教财经,而且是要教专业知识很强的金融学。
虽然没有教好这个书的把握,但黄达还是没有过多考虑,就开始了新工作。
“在那摧枯拉朽、地覆天翻的年代,个人的荣辱得失和事业理想都显得非常的渺小。虽然也想革命成功之后还是学工,但当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际,分配我从事经济理论教学,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一决定终身职业的安排。”他回忆说。
也是从那时起,黄达再也没有离开过教学和金融。

后来,黄达常用“土法上马”来形容自己不懂但却要教的那段经历。
如何“土法上马”,简单说,就是先用十足的力气去学习,学会之后再去当老师,用十足的耐心教别人。他说,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路子,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都学苏联,金融专业教材也是完全照搬,黄达最初也是如此,但他更早开始了对苏联理论和中国实际的思辨,对西方经济与金融的学习和研究,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独特思考,这也是他能成为一代先驱大师的关键。
1955年3月,黄达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国货币的本质与职能》,并作为研究主力撰写了《经济建设初期农村中的货币流通》,迈出了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第一步。
1957年,黄达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人民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货币商品的符号》一文,跳出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局限,对中国实际经济工作的货币问题进行了探讨。
期间,黄达还高压锅式地系统了解、学习与研究西方货币信用制度,并且作为总纂定稿人,主编了《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流通与信用》一书。
黄达说,这本书的编写使他收获很大,因为写作既是创作的过程,又是学习与吸收的过程。这本书,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改编的一本金融学科方面的教材,出版即被全国普遍采用,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依然是金融专业学生的“启蒙书”。
1958年,早就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着共性的黄达,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如果不讲共性,社会主义货币流通的“个性”也很难讲清。
但当时的金融教材都被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而后者多是反复在讲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很少讲专业共性问题。
黄达于是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事,完成一件更加了不起的大事:
将《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合并成一门课,并且主要讲货币银行领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所共同的东西。
这就是黄达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货币流通与信用融合起来分析的专著,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本金融教材的——《货币信用学(上册)》。
《货币信用学》不但在体例上与苏式教材体现出很大差别,也在内容上突破了照搬苏联讲义的桎梏,为新中国的货币银行学的建立起到了关键性的奠基作用。
但遗憾的是,受到金融教师同行欢迎的《货币信用学》却没为当时的黄达带来好运。
在当时,这样大胆的理论尝试,还是被认为犯有混淆两种社会制度本质区别的政治错误。黄达也于1960年秋的一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持续半年的严厉批判,其下册也因此夭折。
但这并未影响黄达对教学和研究的投入。1958年到“文革”前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破坏,更多人开始感受到,国家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无法从马列经典著作或苏联版的经济理论中找到解决的答案。
黄达因此更加认真地思考起中国经济及货币金融问题,更加认真地反省了教条式地引用马克思主义和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病,并更加坚定了从现实出发,扎扎实实从事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的学术追求方向,致力探索适合中国现实经济生活的货币流通问题。
1962年,黄达结合自己的研究,发表了他在那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章——《银行信贷原则与货币流通》。这篇文章中,他一方面强调要尊重并按客观规律办事,一方面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只承认现金是货币的货币观点提出了质疑。其结论是:现金量与存款量之和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货币量,构成与商品流通相对应的统一的货币流通。
黄达的这些观点在后来得到共识并被写进教科书,但在当时,依然引起了广泛争议。
当争论还在继续,黄达却将研究投向了更广泛的领域,并于1964年写了《如何看待价格》一文。这篇文章系统地探讨了货币与价格等关键问题,提出了后来成为普遍常识的真知灼见,但很遗憾,这也成了一篇十几年没有发表,只在1988年才收入《黄达选集》的文章。
因为,就在他准备再接再厉时,一场大的破坏运动爆发了,黄达开始挨批判、写检查、关“牛棚”,被进干校劳动,这对于正处于黄金年龄段的他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但黄达仍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和追求真理的信念。
1973年,刚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他就整理出自己用几年时间呕心沥血研究和准备的《旧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工农产品比价资料》(手稿),用事实否定了当时流行的“剪刀差已经消除”的论断,并深度分析和评判了当时中国物价的现状。
颇有“塞翁失马”意味的是,那期间,黄达还巧妙地利用当时的“评法批儒”,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并与其他同志合作编写了《商君书经济思想论述选注》和《历代法家经济思想选注》。
这些来自于历史和哲学的丰富知识,让他的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也对他后来研究中国经济现实问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人民大学复校以后,黄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校园和讲台,其教学研究工作也迎来新的春天。
但这条道路依然不是那么平坦。刚刚“复出”,他就惹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1979年春天,有关部门在无锡召开了一次以讨论按劳分配和价值规律为主的经济学家研讨会。参会的中国人民大学代表,为了多带几篇文章上会以壮行色,让黄达也赶写一篇。
黄达于是认真写了一篇题为《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货膨胀问题》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多年来,中国各种商品的生产条件、市场需求、劳动生产率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而各商品的价格却长期不变,比价很不合理。要使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调整不合理的比价,并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对此文章,有的学者赞成,更多的人则尖锐批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原打算在试刊号刊登,但因通货膨胀一词闯了禁区,没有人敢冒险行事,直到第6期时,才删除掉“通货膨胀”字眼,以《试论物价的若干问题》这个羞答答的标题公开发表。
虽然当时提出物价改革观点颇为超前,且难以被有些人理解和接受,但黄达却表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品格。他也因此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次提出价格改革的经济学家之一,当然,也有人将他称为是“鼓吹”通货膨胀的先驱。
多年后,他的这篇文章更是获得殊荣:于1998年获得第一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
通过在物价问题上的“鼓吹”,黄达还被邀请加入中国价格学会担任常务理事。
中国价格学会第一次召开常务理事会,学会会长发言说:我们这个学会是坚持党的双百方针的,我们的物价工作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要听取……
黄达笑着回忆说:“我当时就是那反面的。”
此间,黄达还得到一个别致的外号。因为他在《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货膨胀问题》一文里,小心加谨慎地写过:“中国的物价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徐徐上涨”,后来的一些学术活动中,黄达常常听到有人小声地嘀咕:
“噢,‘徐徐上涨’来了。”
此后,黄达又接着写了一篇专门论述劳动生产率、积累、消费和物价水平相互关系的文章——《积累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后来,黄达主编《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一书时,也在书中专门设立了“货币与价格”的章节,进一步系统深入地阐述了自己的物价思想。
《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由黄达和陈共、侯梦蟾、周升业、韩英杰等合作编写,是具有教材性质的专著,出版后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好几届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并先后于1987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88年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1989年获得中国财政学会全国优秀理论研究成果荣誉奖。
从1981年开始,黄达先后发表多篇有关综合平衡问题的文章:如《综合平衡和货币流通》,《什么是信用膨胀、它是怎样引起的》(与周升业合作),《财政收支与信贷收支相互配合中的接合部问题》(与韩英杰合作)、《中国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和通货物价控制问题》等。其中,后者还荣获了孙冶方经济科学的1984年度论文奖。
1983年,黄达结合有关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论述,编写了《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书。该书集他多年从事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之大成于一体,被认为是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体系,并长期在中国货币金融思想史上占据着指导性位置。
这本书,也是让黄达日后被公认为一代泰斗和宗师的核心原因。
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因为书中的分析模式与西方的IS—LM模型有相似之处,一位香港人士看了黄达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后,误以为他曾留学英美专门深造金融学。
黄达笑着对他说,我哪也没去过,学的东西是从苏联传过来的,但也没去过苏联。对方问,他为何能有西方的理论知识背景,他回答说:“只要存在着同样的经济活动,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思考,就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事实上,这是黄达的谦虚,他对西方学说却是孜孜不倦。他的博士生弟子之一,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就曾回忆说:
“英文版的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语言晦涩难懂,鲜有人能通读该书原文,查阅人大图书馆的英文版《通论》,扉页上插着一张发黄的借书记录,寥落的几个姓名里赫然有着黄达的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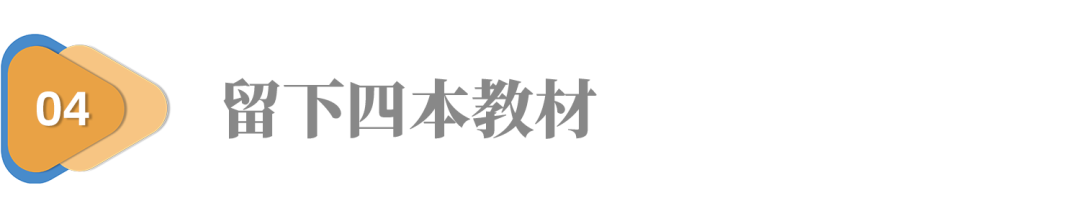
《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写作后期,黄达被任命为人民大学副校长,但行政事务的增加,没有影响他在金融学的世界里继续探索,只要稍有空闲,他就会继续教学和研究。
“每年我都给袁(宝华)校长打一份报告,说已经干了一年了,不想干了。可袁校长说,再过一段时间,我也不干了,咱俩共进退。只好再干下去了。”黄达说。
即便实在公务太多,文章不写了,教学和研究也没放下来。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但国内金融院系所使用的金融教材却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编出一套既在内容上与时俱进,又能适合中国实际的教材,就成为金融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直将金融学科建设视为重点的黄达,于是推动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接受了当时国家教委关于财经专业十门核心课程中的货币银行学教材的编写任务,并亲任主编,会同周升业、沈伟基、王松奇、李焰四人一起,肩负起了编写更先进金融学教材的使命。即便1991年底,年近67岁的黄达被任命为人民大学校长,教材的编写仍被他视为重中之重。
1992年,这本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先进的金融学教材——《货币银行学》终于诞生了,并被指定为“国家教委审定高等学校财经类核心课程教材”,迅即推广至全国,成为全国高校财经类学科的经典教材。
出版《货币银行学》期间,黄达还主编了他所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的成果——《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
1994年年底,黄达从人民大学校长的职务上退了下来,但他并没有去颐养天年,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他钟爱的金融教学和研究上。
1995年,黄达出任了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并作为主编之一,指导和参与了大型工具辞书《中华金融辞库》的编纂;1997年,他撰写出版了《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
他在《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中强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不可割裂,概括地说都是发展的问题,而发展的焦点则是速度问题,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
他说,讲速度,绝不单纯是主观的愿望,而是生活本身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没有必要的速度,难以坚定改革的信心;没有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稳定也就不具备牢固的基础。
《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写作、出版期间,黄达还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对《货币银行学》作了修订,并最终完成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历时3年,带领同事们将《货币银行学》升级为《金融学》,为21世纪初的中国金融学学科建设再次贡献了一本经典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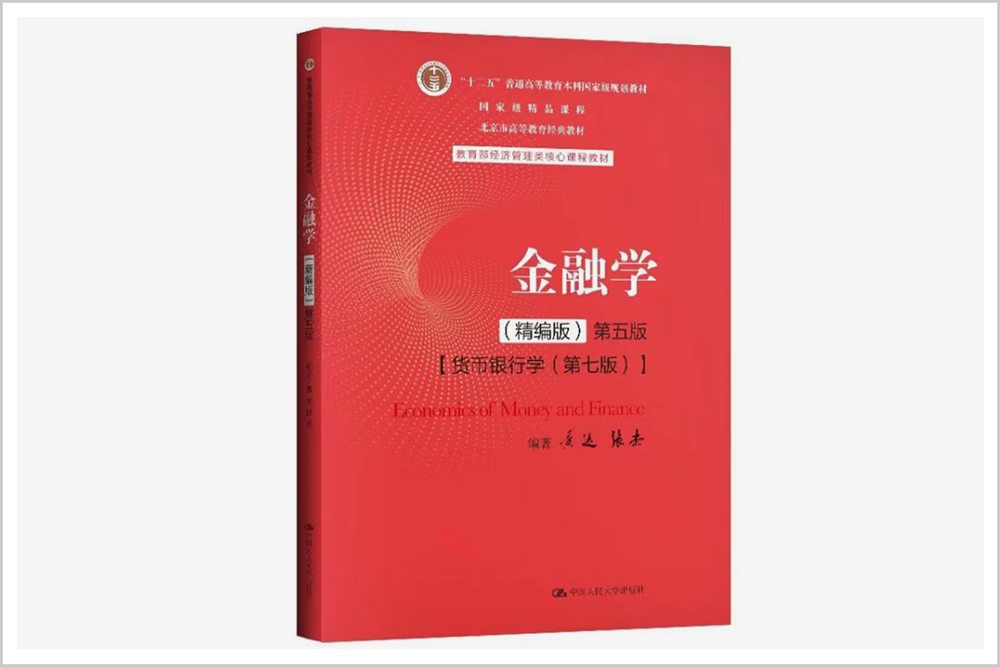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到《金融学》出版时,黄达已是81岁的高龄了。
很多人可能认为,他这个主编是挂个虚名。但事实却远非如此。黄达当主编有个很大的特点,他要求参与编写的人提供素材,但用还是不用,怎么删改,最后由他亲自决定。
因此,他编的教材里总是既有集体的实践和总结,又有很多他个人的思想、科研成果。为此,曾有人开玩笑说,别人的书可以抄,但黄达的书不能抄,他的书里都是他自己的真知灼见,行文语气都是他特有的风格,一抄就看出来了。
除了发表专著,编写教材之外,黄达还出版有《黄达选集》,以及约400万字的《黄达书集》,直到2010年,他还出版了《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
但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教育研究与学术成果之时,著作等身、位及人大校长的他,却总是谦虚又自豪地表示:只留下四本教材——《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货币银行学》、《金融学》。
这4本教材,从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之初,影响了几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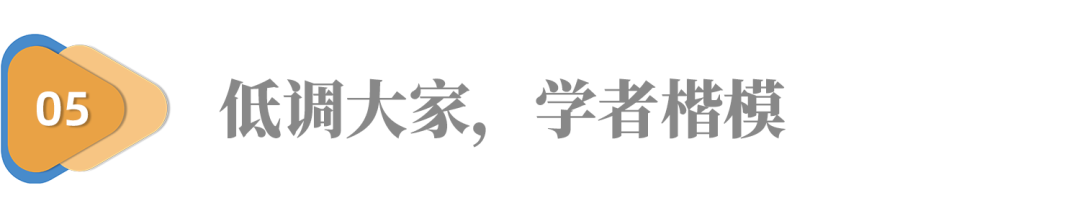
黄达说,自己能有所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颇得益于教学。”
他有一套“教学相长”的方法和理念,贯穿终生。
“如果确实真心诚意地想把学生教懂,首先得自己懂。自己懂了远远不够,还要通过文字,特别是要通过口头表达自己之所懂。所以说,从备课,到编教材,到讲授,到主持讨论,到组织考核等等,每个环节都是从‘自己懂’向‘使人懂’的转化。”
几十年的教育和研究生涯中,不论行政工作或社会活动如何多,黄达始终把不脱离教学第一线作为自己遵守的准则。从走上讲堂到走下讲堂,他都是在教与学中度过。
先学后教,边学边教,教到老学到老。
黄达不赞同过分渲染教学与研究的矛盾。他常说,研究工作务必要打好理论基础,而教学恰恰是打好基础的最佳途径。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自己多付出时间和心血。
他总是告诫学生:“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论及教书育人,黄达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他不但在人民大学的讲台上,为国家培育出了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大学校长、以至国家的高级干部等大量高层次经济金融人才,更通过全国通用金融教材,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几乎所有金融专业的学生。
但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博士后导师,黄达的嫡传弟子却不多。
这主要源于他对教育的严谨态度,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带不了那么多的学生,所以干脆不带,他说:“招人而不育人与一个老师的责任不符”。
想成为黄达门下弟子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包括不少官员和商界名人,但他都是婉言谢绝。理由也是,“他们是没有时间认真做研究的,能不能写出论文来还要打个问号,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头衔,但这与我的想法并不一致”。
他知道这样可能把一些确实想提高专业水平的人拒之门外,但他还是坚持。
黄达不仅是学术上的导师,更是道德上的楷模。其治学的严谨和诚实,为人的真诚与热情,一直是学界的榜样。1999年,黄达出版了《黄达文集》,让人意外的是,他特意把大跃进时期所写的被自己称为是“满是呓语”的文章也一并收录进来,自揭其短。
他说,这样“可以自警,也可以使没有这类经历的人对于那种岁月的思想紊乱多少获得点形象的概念”。
《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一书是他受侯梦蟾、周升业两位先生的一篇论文启发,进而深入思考研究写成的。为此,他特地在著作中提到两位先生的文章,并将其附于专著之后。
他经常告诫他的弟子们,做人要端正,切忌做“墙头草”,不要为获一时之利留下终生遗憾。
在金融已经成为显学中的显学时,作为知名金融学家的黄达,不断接到慕名请他担任顾问或董事的邀请,但他统统拒绝了这样的“变现机会”。
他还有个“三不”原则:不兼职、不写序、不写推荐信。“写序,自然要写好话,只签名呢自己又觉得不妥,真要自己写还要花时间认真读这本书,我又没那么多时间。”他说。
而且,黄达还有一个“坚持自己干,不依赖他人”的习惯。
他写东西不用人代劳,出门在外也不愿意属下或工作人员帮忙提行李。
黄达不认为真正的学者能够不受环境与时代的影响,但他也绝不相信一名“贾桂”式的学者能安身立命。爱好京剧的他,对京剧《法门寺》中小太监贾桂的奴才思想印象深刻,他提倡做学问应当独立思考,实事求是。
黄达一直谦虚地称自己为“教书匠”,而且的确不像一些专家学者那样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但事实上,他在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之外同样卓有建树。
他不但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还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和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中国金融学会会长等职务,还经常作为各届政府决策部门征询意见的学者,在国家现实经济生活方面发挥、贡献了智慧。
自称“哪里也没去过”的黄达,还十分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远见能力。
1983年出任人民大学副校长期间,他就前瞻性地提出:“我们要将学生造就成能够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的人才。”并且十分强调大学校园的国际性对推进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身体力行地推进人民大学与世界各国大学的交往。
他说:“人类的智慧、学识和文明,永远是超越国界的……要建立真正的现代化大学,必须实现校园的国际化。”
*华商韬略出品丨ID:hstl8888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