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41年春天。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打得如火如荼,美国也很快就要参战。世界被炸得四分五裂,混乱像拳头一样打在每个新出生的人的脸上。如果你在这时候出生或生活在这个年代并还活着,你就能感觉到旧世界即将离去,新世界即将来临。这就好像把时钟拨回到公元前后的交替时代。每个和我同时代出生的人都是新旧两个世界的一部分。希特勒,邱吉尔,墨索里尼,斯大林,罗斯福——这些后无来者的巨人,他们都只依靠自己的决心,无论好坏,他们每个人都准备好单独行动,对他人的赞许无动于衷——对财富或爱情无动于衷,他们掌控着人类的命运,将世界碾成一堆碎石。他们与亚历山大、裘力斯·恺撒、成吉思汗、查理大帝和拿破仑一脉相承,像对待一顿精美的晚餐一样瓜分了世界。不管他们梳着中分的头发还是戴着海盗头盔,他们的意志都不会被拒绝,也不可能预测——粗鲁的野蛮人踏过土地,敲定出他们自己定义的世界地图。
我父亲患有小儿麻痹症,这让他远离战争,但我的叔叔们都去参战而且都生还了。保罗叔叔,莫里斯叔叔,杰克,麦克斯,路易斯,韦农,还有其他的叔叔们去了菲律宾、安希奥、西西里、北非、法国和比利时。他们带回各式各样的纪念品——一个用稻草编织的日本雪茄盒,德国面包袋,英国的陶瓷马克杯,德国的防尘护目镜,英国战刀,一把德国卢格尔手枪——各式各样的垃圾。他们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回到了文明社会,对于他们做过什么、见过什么从不吐露一个字。
1951年我上小学了。我们学的一件事就是当空袭警报响起时要躲到书桌底下,因为俄国人会用炸弹攻击我们。我们还被告知俄国人随时都可能从飞机上跳伞,降落到我们所在的城镇。这些俄国人就是几年前和我的叔叔们并肩战斗的俄国人。现在他们变成了来割开我们的喉咙、烧死我们的怪兽。
这好像很奇怪。生活在这样的恐惧阴云下剥夺了一个孩子的精神。害怕有人拿枪指着你是一件事,但害怕某件不太真实的事就是另一码事了。我周围有很多人把这种威胁看得很严重,而这会传染给你。很容易你就成了他们奇怪幻想的受害者。我在学校里的老师就是以前教我母亲的老师。教我母亲的时候他们还很年轻,教我的时候都已经老了。在美国历史课上,我们被教育说共产主义国家单靠枪和炸弹是无法摧毁美国的,他们必须摧毁宪法——美国的立国之本。但是这并没改变什么。当警报响起时,你还得脸朝下躺在书桌下面,不能有一块肌肉颤抖,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好像这样就能在轰炸中救你一命。被歼灭的威胁非常吓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让他们这么疯狂。人们告诉我们,红军无处不在,而且极度嗜血。我的叔叔们都到哪儿去了,这些国家的保卫者?他们在忙于生计,工作,得到他们能得到的,并尽力维持。他们怎么会知道学校里在教些什么,怎样的恐惧正被激起?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在纽约市,共产主义者或非共产主义者。周围可能都有不少。还有不少法西斯主义者。不少未来的左翼独裁者,或右翼独裁者。各种各样的激进分子。有人说二战宣告了启蒙时代的终结,但我从来不知道。我还在启蒙时代里。我多少还能记得并感受到启蒙的光。我在读那些书。伏尔泰,卢梭,约翰·洛克,孟德斯鸠,马丁·路德——这些空想家,革命家......我好像认识他们,他们就像住在我家后院一样。
我走过地板来到奶油色的窗帘前,拉开那威尼斯式的软百叶窗帘带,看着外面下着雪的街道。这地方的家具很好,有一些甚至是手工做的。那也很不错——嵌花的衣橱,上有风格化的雕纹和华丽的把手,到天花板高的装饰性的书架,一张含有金属材料的狭窄长方形桌子,上面的几何图形似乎遵从着某种自然规律,还有一件有趣的物件,一张螺形拖脚小桌设计得像是一个大大的脚趾。壁橱的架子上巧妙地放置着电板。那个小厨房则像是个森林。放蔬果的盒子里装满了薄荷、香车叶草、丁香叶和其他东西。克洛伊,一个有着北方血统的南方女孩,非常擅于使用浴室里的晾衣绳,有时我会发现我的某件衬衫挂在那儿。我通常会在天亮前回来,一头扎进沙发,它就在那个高高的带门廊的厅里,可以翻开成为一张折叠床。我经常伴着穿过泽西的夜班火车隆隆开过的响声入睡,那匹嗜血的、冒着蒸汽的铁马。

在我最早的童年时光我就看见过火车,听过火车的声音,火车的样子和声音都让我感到安全。那大大的箱式火车,铁矿车,货车,客车,普尔曼式卧车。在我的家乡,你总会在一天某个时候某个十字路口等待长长的火车通过,然后才能去到你要去的某个地方。铁轨有时穿过乡间的道路,有时和它们平行。远处传来的火车声多多少少会让我有在家的感觉,就像是什么也没失去,就像我坐在某个平坦的地方,从未碰到什么真正的危险,而且一切都很和谐。
我透过窗户看到的那条街对面是一座带钟楼的教堂。那钟声也让我有在家里的感觉。我总是听见钟声,并愿意倾听它们。铁的、铜的、银的钟——钟会歌唱。在星期天,做礼拜的时候,还有节假日。当某个重要人物去世时,当人们结婚时,它们就会地敲响。任何特别的场合钟声都会响起。你听到钟声时会有愉快的心情。我甚至喜欢门铃声和收音机里NBC的报时钟声。我透过用铅框固定的玻璃窗望向对面的教堂。那钟现在沉默着,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屋顶。一场大风雪绑架了这座城市,生活围绕着一块灰白的帆布在转。冰冻寒冷。
路对面有个穿皮夹克的家伙正在给一辆积满雪的黑色水星蒙克莱尔车铲去挡风玻璃上的冰霜。他后面,一位身着紫色袍子的牧师穿过敞开的大门,快步走过教堂的院子,赶着去履行神职。不远处,一个穿着靴子、没戴帽子的女子使劲背着一个大洗衣袋往街上走。每天纽约都发生着一百万个故事,只要你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身上。这些故事一直都在你的眼前,混合在一起,但你得把它们分开,以赋予它们某种意义。情人节,恋人们的日子,来了又走了,而我根本没注意到。我没有时间去浪漫。我从窗口转过身,离开冬日的太阳,走过房间,到炉子边给自己弄了杯热巧克力,然后扭开了收音机。
我总在收音机里寻找着什么。就像火车和钟声,收音机也是我人生音轨的一部分。我把接收频道的指针上下移动着,罗伊·奥比森(Roy Orbison)的声音就从那两个小喇叭里蹦出来了。他的新歌《胆战心惊》在房间里轰鸣着响起。最近我一直在听那些具有民歌意味的歌。在过去有一些这样的歌:《大个子坏约翰》,《麦克摇船靠岸》,《一百磅泥土》。布鲁克·班顿(Brook Benton)把《圆荚象虫》唱成了当代流行金曲。电台里也开始播放“金斯顿三重唱组”(The Kingston Trio)和“四兄弟演唱组”(Brothers Four)。我喜欢“金斯顿三重唱组”。尽管他们的风格有点矫饰和学生气,我还是喜欢他们的大多数歌曲。像《逃跑的约翰》、《想念阿拉莫》、《黑色来复枪》这些歌。总有一些民谣类型的歌曲会跳出来。《无尽的睡眠》,这首乔迪·雷诺兹(Jodie Reynolds)的歌几年前就大红大紫,风格上也是首民谣。而奥比森则超越了各种风格类型——民谣、乡村、摇滚或者任何东西。他的歌融合了所有的风格,其中甚至还有一些未被创造出来的风格。他可以把某一句唱得粗俗恶劣,而下一句却用起了弗兰基·瓦利(FrankieValli)那样的假声唱法。听罗伊唱歌,你不知道是在听街头音乐还是歌剧。他能让你时刻全神贯注。说起他,一切都有血有肉。他听上去像是在奥林匹斯山顶歌唱,而他就意味着生意。他的一首早期歌曲《乌比杜比》很早就流行起来了,但他的这首新歌却完全不同。《乌比杜比》听上去很简单,但罗伊在前进。现在他把曲子唱成三个到四个八度让你听了想把车开下悬崖。他像一个职业罪犯一样唱歌。通常,他会用低沉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开始,在那个音域停留一阵子之后,接着突然滑入夸张的高音里。他的声音可以震醒一具尸体,总能让你禁不住喃喃自语:“伙计,这真难以置信。”他的歌里还有歌。它们毫无逻辑地从大调转到小调。奥比森非常严肃——他可不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电台里播的歌手再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我等着想听他的下一首歌,可罗伊之后,电台播放的曲目实在是无聊..….没种,软弱。那些歌放出来就好像你是没有脑子的。也许除了乔治·琼斯(George Jones)之外,我也不喜欢乡村音乐。吉姆·李维斯(Jim Reeves)和埃迪·阿诺德(Eddy Arnold),很难说那些东西和乡村有什么关系。所有野性和怪异的元素都从乡村音乐里消失了。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也没有人听他了。他扭胯和将歌曲带到其他星球的事离现在已经有些年头了。我仍然开着收音机,也许更多是因为无意识的习惯。令人感到悲伤的是,不管它播什么都只是牛奶和糖,并没有真正体现这个时代双重性格的歌曲。《在路上》(On the Road)、《嚎叫》(Howl)和《汽油》(Gasoline)代表的街头意识形态标志着一种新型的人的存在,它们不在这里,但你能期望什么?每分钟45转的唱片做不了这些。
我为出唱片而痛苦挣扎着,但我不会想出单曲唱片,45转的——那种在电台里播的歌。民谣歌手、爵士艺术家和古典音乐家都出密纹唱片(LP),那种长时间播放的有许多首歌的唱片——他们以此铸造出自己的风格,取得决定性的优势,传达出更宏伟的图景。密纹唱片就像重力。它们有封面、封底,前后都有,你可以盯着看几个小时。放在它们旁边的45转唱片显得薄而不成形。它们只是堆成一堆,看上去一点都不重要。我的曲目里没有一首歌是给商业电台的。堕落的私酒贩子,淹死亲生孩子的母亲,每加仑汽油只能开五英里的凯迪拉克,洪水,工会大厅的火灾,河底的黑暗和尸体,我歌里的这些题材可不适合电台。我唱的民谣绝不轻松。它们并不友好或者成熟甜美。它们可不会温柔地靠岸。我猜你会说它不商业。不仅如此,我的风格违反常规,无法被电台简单地分类,而对我来说,歌曲不仅仅是轻松的娱乐。它们是我的感受器,指引我进入某种与现实不同的意识中,某个不同的共和国中,某种自由的共和国。音乐史家格雷尔·马库斯(GreilMarcus)在三十年后会称这共和国为“看不见的共和国”。不管怎么说,这并不说明我反流行文化或其他什么,而且我也没有野心去挑起事端。我只是觉得主流文化很落后,是个骗人的把戏。它就像窗外那坚固的冰霜,你不得不穿着笨重的鞋子走在上面。我不知道我们处在历史的哪个阶段,也不知道它的真相是什么。没人在意这些。如果你说出真相,那很好,如果你说出的不是真相,那也很好。民谣教会了我这些。至于说现在是什么时代,答案永远是曙光初开,而我也知道一点历史——几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它们总是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最早的古代时期,社会发展并达到繁荣,然后进入古典时期,社会到达它的成熟点,接着就是松弛期,衰落使一切分崩离析。我不知道美国处在哪个阶段。没有人能核实这个问题。但有某种粗暴的节奏撼动着整个国家。想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怎么想都可能错得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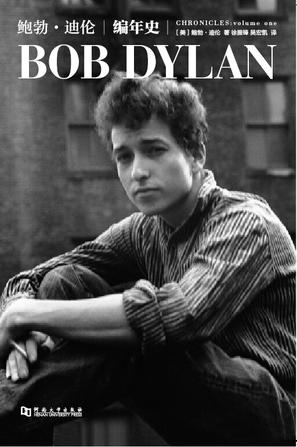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编年史》(鲍勃·迪伦 著,徐振锋 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