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展雄,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欧洲中世纪有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Stadt Luft macht frei)。”乍一听,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城市空气是污浊、恶臭的,满街粪便污水横流,楼上居民窗口倒马桶。居民在自家后院堆积垃圾杂物,托马斯·莫尔曾担任治安副官后,对伦敦的肮脏深有体会,他在著作《乌托邦》里,特别强调了城市卫生工作。
伦敦城的污秽大部分运到泰晤士河,河口有一间茅房靠近修道院,1275年他们向爱德华一世报告:“此地的腐臭盖过了宗教仪式所焚的乳香,曾熏死多位修士兄弟。”

▲ 在下水道系统和抽水马桶发明之前,如厕的解决方案简单粗暴——人们直接将大部分排泄物倾倒进河里。图为作于1461-1475年间的手抄绘本,描绘了市民在伦敦桥上的公共厕所如厕时不小心掉进泰晤士河。 John Lydgate
一个伦敦人出行最大的担忧,就是怕走路遇到垃圾车、运粪车。车辆稍微一个颠簸,就能毁掉你的衣裙和一天的好心情。就算躲得过垃圾、粪便,也躲不过笼罩全城的雾霾,在工业革命之前,伦敦就享有了“雾都”的名号。染坊、石灰厂制造了大量废气,很多富人的豪宅被煤烟熏得乌黑,1661年文人约翰·伊夫林向国会提交空气质量报告,用“地狱般阴惨惨”来形容伦敦城景象。
北美独立战争结束后,杰斐逊(美国开国元勋,第二任总统)出使英国,对伦敦的肮脏贫穷大感意外,从此坚决反对工业化、城市化:“让工厂留给欧洲,我们美国有农业就足够了。”
在现代化城建兴起之前,乡村更适宜人居。城市由于人口、住宅高度密集,各种灾祸更容易发生。14世纪的黑死病杀死了伦敦一半居民;1666年伦敦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蔓延了80%的城区;1952年毒雾遮天蔽日,1.2万人生病致死。每当天灾出现的时候,居民都是从城市逃到农村,而不是相反的路径,莎士比亚的部分戏剧,便是在躲避伦敦瘟疫期间写的。

▲ 伦敦寒冷漫长的冬季使得居民需要大量烧煤进行取暖,加之地理和气象因素,冬日的伦敦经常大雾弥漫,数日不散。图为1952年冬天,伦敦东区一家工厂在浓雾中继续排放着烟尘。而随后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毒雾之灾降临伦敦。 metoffice.gov.uk
饶有千般险恶,仍有人义无反顾地去城市闯荡。因为乡村是受束缚的,封建制度(feudal)像一副枷锁套在了农夫的脖子上,只有跑到城市,才能自由地喘口气。中世纪的城市有自己的法院、监狱,自行处理内部事务,领主的强横、主教的权威被隔离在护城墙之外。不必等到工业革命,西欧的布尔乔亚早在数个世纪之前,就有自选自治的权力。
市长是由众人推举而来,在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职位每年选举一次。十六世纪,伦敦城划分为26个区,每区一个议员。整整一百年来,市长都来自于平民阶层,有24个市长是绸缎、丝绒商,17个是呢绒商,14个是食品杂货商,没有一个王公贵族。直到亨利八世上台后,王室才对市长一职有了举荐权。
欧洲比较出名的自治市镇有尼德兰联省、德国汉萨同盟,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自选自理,只有敢于抗争的才会获取自由,法国巴黎在13世纪末还没有得到独立地位,而伦敦早在1067年,就从威廉一世获得特许状。迟至14世纪,市政厅的书记员称呼伦敦为Republic,可见其城邦自治的传统。这个机构在19世纪改组为伦敦郡议会、都市工程委员会,在1965年演变成今天的大伦敦(Greater London,包括伦敦市和32个次级行政区)议会。
虽然西欧的城市,比起同时期的长安、巴格达、君士坦丁堡,外观寒碜、规模狭小,但它里面住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勇士,而东方式专制政体有的只是怯懦的小市民。一份亨利三世时期的法令显示,伦敦城的每位长老,都要检查马具、兵器,确保人人有剑,防备贼寇。1590年代,有一个纺织工冒犯了伦敦市长,当局来抓他的时候,纺织同业公会三五百人打退了市长的警卫队。
君王不喜欢这种桀骜不驯的城市,狮心王查理曾说:“如果找得到买家,我愿意把伦敦出售掉。”他的弟弟约翰是由首都民众拥戴为王的,就是在约翰时期,《大宪章》签订,君主的权力受限制。当约翰征收更高的租金、税额时,市政厅决定赶走他,邀请法国的王子路易为新君。为了给他支付路费,伦敦富商凑了一千马克,当年冬天约翰病逝,也就没有更换王朝的必要,伦敦人给了路易更多的钱,让他回家。
外国人对此啧啧称奇:“伦敦人不要国王,只要市长。”都铎玛丽女王时期,有一位大臣厌恶伦敦,计划把首都机构搬迁到牛津,市议员和颜悦色地回复道:“那就尽管走吧,你能搬得走王宫,也能搬得走政府大楼,但是你没法搬走泰晤士河。”
泰晤士河是伦敦力量的源泉,这条河流上船只往来,帆桨忙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泰晤士河大约有8000个船夫。在18世纪初,伦敦码头运输全国80%的进口物资、69%的出口物资。河水极少结冰,即便发生这种情况,商人也不会停止,人们坐在马车上在泰晤士河奔驰。

▲ 1928年10月,伦敦塔桥附近的泰晤士河边,几位市民在大雾中给天鹅喂食。 metoffice.gov.uk
只要泰晤士河水不干涸,伦敦就能对抗王权。在内战时期(1642-1651),查理一世果真迁都至牛津,因为伦敦支持议会,成了革命派的大本营,1649年克伦威尔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共和国。
王政复辟之后(1660-1688),斯图亚特家族回到伦敦,但是把家宅安置在市中心外,直到今天依然如此。2002年,政府举办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典礼,伊丽莎白二世到达老城门口时,在侍从搀扶下走下马车,向市长请求入城的许可。这种象征性仪式表明了伦敦的神圣不可侵犯,她是唯一一个需要这样许可的英国人。
自建城之日起,伦敦就在捍卫自身独立性,因此中世纪才会有“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条谚语。人们从英格兰各地迁徙到首都,18世纪初,每年近1万人搬进伦敦,1750年,伦敦人口占了全国十分之一,在维多利亚黄金时代,首都住有五百万居民。
那会儿的英国人看待伦敦,就像今天的我们看待北上广,大城市既有更多的机遇,也有更多的龌龊,南海泡沫、东印度公司、东区贫民窟,金钱罪孽都发生在此。约翰·班杨在《天路历程》讥讽伦敦的虚荣,狄更斯控诉资本家的贪婪罪恶,但是伏尔泰却对此称赞不已。他参观了伦敦交易所后,发现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分宗教偏见,齐聚一堂,这里唯一的异端是破产。
英格兰的宗教中心不在这个政治中心,坎特伯雷大教堂位于伦敦东南一百公里的市镇。伦敦人关心金钱甚于关心灵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唯利是图。居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当1831年霍乱传播后,伦敦组建了世界最早的卫生疾控中心;1952年的“大雾霾”后,英国人制定了世界第一部空气污染治理法案。
市政管理最成功的例子是对垃圾的变废为宝,1760年伦敦进行综合整治,通过技术改良,粪尿变为肥料,煤灰、灰烬可以转变为砖头,垃圾成了赚钱的行当。18世纪,报纸上刊登垃圾处理商的广告,招徕生意。皮卡迪利广场是伦敦清洁工的聚集地,他们有时候为了争夺垃圾,互相打架。19世纪初,白教堂区(也是开膛手杰克的作案地带)附件的煤灰堆积成山,俄国人买下了这座山,用以制成砖石,修葺被拿破仑焚毁的莫斯科城。商业精神没有削弱伦敦的力量,而是增强了它。
电影《天国王朝》里,主人公说:“我们保护这座城市(指耶路撒冷),不是为了保护这些石头,而是生活在这的人。”失去了精神灵魂,城市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伦敦的伟大不是因为它有白金汉宫、英格兰银行、大英博物馆,而是因为它有最卓绝优秀的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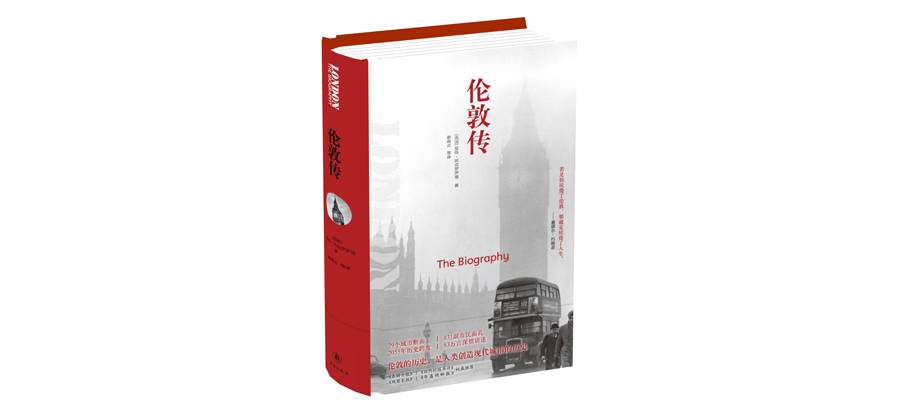
本文是对《伦敦传》一书的评介,伦敦的历史,是人类创造现代城市的历史。英国传记作家阿克罗伊德曾为英国的莎士比亚、牛顿、狄更斯写作传记,这一次,他为伦敦作传。作者用恢宏的城市历史、敏锐的观察、无数市民和访客的话语,揭示了伦敦如何在从远古到现代的历史洪流中淬炼成形。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