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今日上午,作家王安忆与余华在华东师范大学思群堂的对谈上再次谈及先锋文学,而王安忆认为余华是先锋作家里唯一一位清醒自觉地找到小说伦理的人。“他开始根据他的现实逻辑叙事了,而很多先锋作家很快就折戟沙滩,包括马原和孙甘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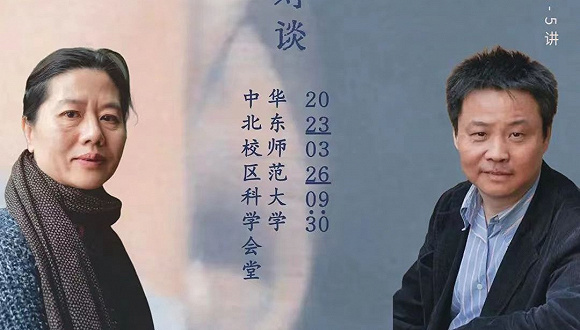
余华:假如没有现实基础,文学像断了线的风筝会飘走
王安忆回忆最初看余华的作品《现实一种》,正是先锋文学风行的时代。那时她对于先锋文学的风潮抱有警惕性,因为怀疑这种叙事的方法不能持久,同时也怀疑其可读性,因为读作品一定从常识出发,而先锋文学的世界跟人们有距离。
王安忆将余华的文学创作从先锋写作到叙事小说的转变形容为从陷阱中跳出,“1980年代我们已经封闭了那么多年,每个人都要反抗,做出与前辈不同的姿态,但他能跳出来,既服从现实逻辑,又能从中跳出,大部分人是不能脱身的。”
而王安忆对于余华作品的评述,则让后者回想起1998年他们一起在中国香港地区等待转机去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形。余华还记得25年前的一个场景——王安忆找到他说,“余华,现在你的小说让我看到人了。”

“余华给人的印象就是找爸爸的男孩子,他的很多小说也都是写父子关系。” 王安忆也对那次的经历印象深刻,当时中国作协组织一批中国大陆作家从北京出发去台北,当时还需要在香港转机,这些作家第一次去台北,感到十分茫然。“大家下了飞机在机场走,迎面走过来一个看起来像浙江农民的人,大包裹小行李的,他看到余华一下子就笑了,说你是去台湾(地区)找你爸爸吧。可见余华给人的印象就是找爸爸的男孩子。”王安忆说道。
余华承认,在写先锋小说时,他觉得自己是笔下人物的主宰,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但写了《活着》和《在细雨中呼喊》后,才感觉到人物有自己的命运。“前面的作品里人人以符号的方式出现,后面的作品人以人的形象出现。”余华讲道,所有的文学,不论是写实还是荒诞的,假如没有现实基础,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会飘走、被人遗忘,所以现实是文学的基础也是出发的地方。作家总要去现实里提取素材,但提取出素材之后处理的方式不同。他以鲁迅的小说《风波》为例,讲述小说与时代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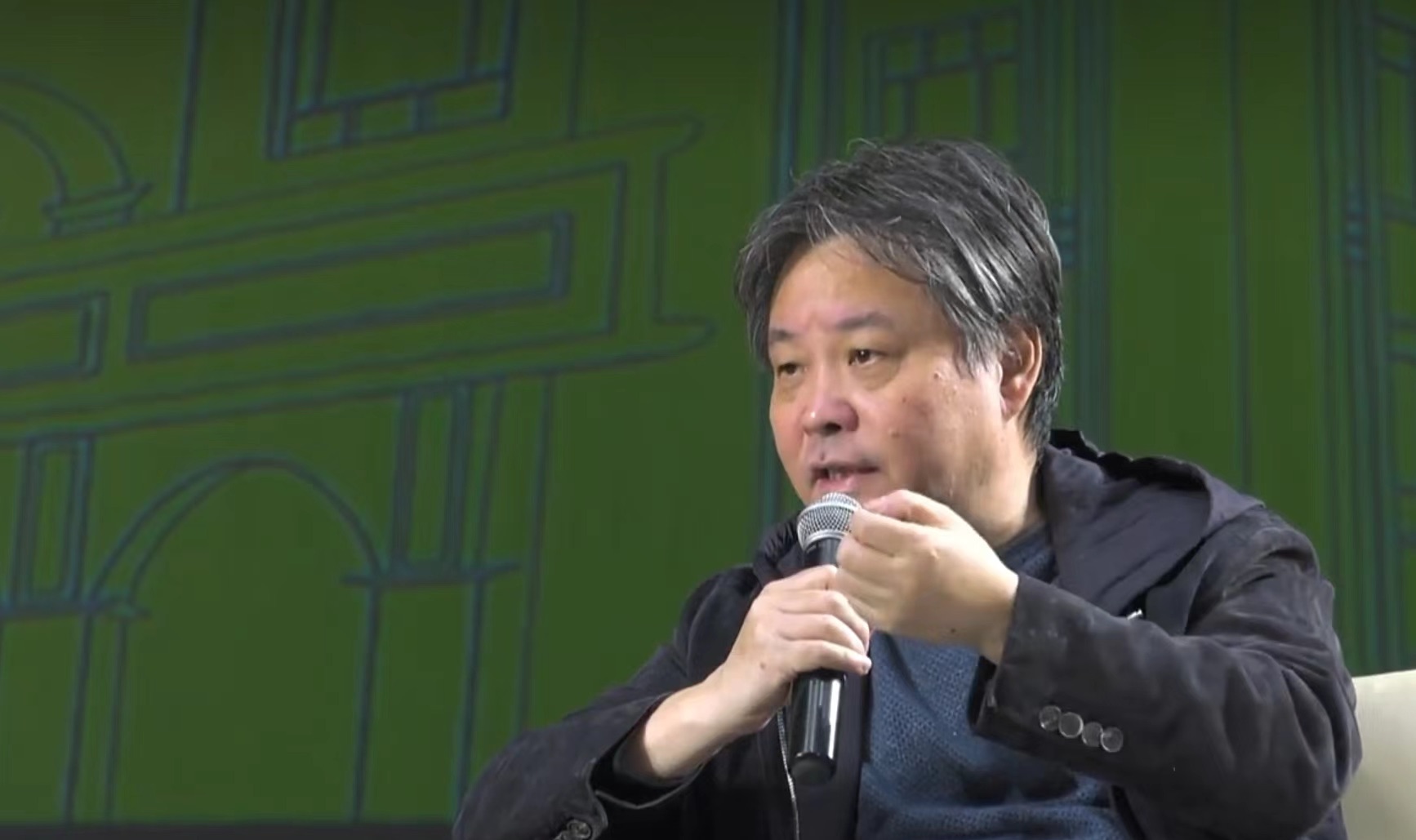
“《风波》里我认为写的最好是赵七爷,皇帝坐龙庭了他要把辫子放下,革命军来了他要把辫子盘上去。鲁迅洞察到了辫子这个细节,写出了普通民众如何面对时代的巨变,这个细节就足够了,不用再往前推了。”而有些素材光提炼还不够,还需要再推一步。余华以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的小说《河流引路人之死》为例,“小说的结尾写得很漂亮,讲的是父亲如何把母亲骗到塔斯马尼亚岛。接近岛屿的时候,有一段描写,写岛上海边那破旧的歪歪斜斜的房屋,以及阴暗的天空,写得都很好,但显然还不够。作者往前推了一步,两人下了船,见到一个男人正在跟电线杆吵架,他的老婆拉住他,不要让他丢脸,他说滚开,这是私人谈话。两人远涉重洋来到这个破地方,本身已经非常不安,下了船听到的又是这样的对话,这是写作中的一种方式。 "
王安忆:当下又有了一种要回到日常生活的写作风潮
与余华所说的将现实再推一步的写法相关,王安忆进一步表示,如果不是有传奇性吸引的话,作家何必要去写枯乏的日常生活呢?她还是渴望着书写一个平民英雄,战争中英雄很多,日常中英雄是很难的。她从自己的写实主义写作中生出的体会是,写作者太被日常逻辑缠绕,特别不容易生长。而据她当下的观察,目前又有了一种要回到日常生活的写作风潮,“这种写作对日常有莫大的尊敬与肯定,也有反启蒙的意义,不能到达精神的一种境界。”王安忆说,前段有人介绍她看小说《同和里》,这部小说写上海市井生活,小孩子在革命波动里的状态,小说的细节特殊,故事的家庭也很特别,但一切都使她感到和现实生活一样地厌倦。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存在着升华的可能,但作者把这个细节给放过了,或许也没注意到,王安忆有些可惜地说道。
“故事里有一个老太婆过着很疲乏的生活,她住在老虎罩的楼上,亲人也很少,忽然有一天,她搬着一条长凳要去小石桥跳河。跳河时有人问她怎么了,她说没意思,要自杀。老太婆也不是个知识分子,也不是个赤贫到没法生存的人,她也没受到很大的凌辱,这个市井中人忽然有一种灵感和神思,觉得做人没有意思。关于活着没意思的问题,知识分子成天考虑,但考虑的都是抽象的,老太经过了那么多年忽然要跳河了。”当下有一种写作非常普遍,它强调日常生活、普通人的不容易与坚忍,但放过了升华的可能。重视传奇性不仅需要想象力,还需要对世界的认识。比如《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故事在忆苦思甜的传统里看过太多了,但余华有一些特别的处理,让主角老实人接纳了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儿子”,还要这个儿子在亲生父亲去世时去喊魂。
王安忆在《许三观卖血记》里读出了传奇性,2021年余华出版的《文城》也被评论家以“传奇”定性。对此,余华说,《文城》的传奇与超越日常的传奇有些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他故意将《文城》写成传奇,因为年轻时读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很受鼓舞,再加上《文城》的年代久远很适合用传奇小说的方式书写。
余华:描摹生活时,小说家比诗人和理论家靠谱
余华发现传奇与叙述关系密切,2022年他录一档电视节目,制作方让他与苏童、西川待在岛上,派欧阳江河和祝勇去了渔村,那两人回来给他们描述渔村的情形却不能令余华满意,“欧阳江河用诗人的方式描述完全不靠谱、祝勇用理论也不靠谱。回来看到王安忆的《五湖四海》写的就是水上渔村,对渔村一展现就清晰了。描摹生活时小说家比诗人和理论家靠谱。”一种传奇如王安忆所说的生活中的传奇,另一种传奇是时间段拉长的传奇,古代历史中的刺客故事就是拉长了时间段的传奇,“我不明白为什么那帮笨蛋老去编荆轲,其实最好的是豫让和聂政,聂政是快刀斩乱麻,豫让是钝刀子割肉。 ”余华说。
王安忆: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涉嫌抄袭
对于时下热门的人工智能ChatGPT王安忆与余华也有各自的评述。“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涉嫌抄袭,因为要搜索内容。”王安忆说。余华虽然没有用过ChatGPT,但是使用过国内的类似软件,不太好用。“我首先问它,文学是个什么东西,结果搜索出现故障。我就问文学有什么意义,搜索又出现故障,可能故障就是最好的回答。”余华认为,人工智能大概能写出中庸的小说而非充满个性的小说,而在文学作品里优点与缺点其实是并存的。很多伟大作品都有败笔,ChatGPT没有缺点,反过来也没有优点。像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有明显的败笔,余华说,格里高尔的尸体处理得太草率了,“当甲虫终于死了,一家人终于过上正常的生活,你不要轻描淡写地说已经处理掉了,那么大一只甲虫,要写如何艰难地把虫子的尸体从门里移走,除非你前面写得比较跳跃,而不是丝丝入扣的。”余华觉得这点是卡夫卡的疏忽,而他写小说时也会有忘记人名的疏忽,“人脑会犯错误,这也是人脑最可贵的地方,因为人不按常理出牌,我认为人工智能起码现在不会对我和安忆构成什么威胁。”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