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健
如今,越来越多原汁原味的外国剧目正借助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南锣鼓巷戏剧节、乌镇戏剧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十余个戏剧节、戏剧展演平台同中国观众见面。
这些演出来势之猛、影响之大,引发了业内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也形成了近年来中国演出市场上一道值得读解的“景观”。
探讨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辨析外国剧目的审美蕴涵固然重要。然而,在开阔眼界、饱览“景观”之余,我们还需要冷静省思:
现阶段,什么样的外国戏剧是我们最需要的?
它们的演出价值是否被我们真正发掘?
中国戏剧距离外国戏剧究竟有多远?

华沙新剧团演出剧照
剧目:引进标准和选戏原则亟待厘清
在话剧传入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戏剧人、观众对外国戏剧的认知与理解,大都是通过剧本、理论的译介建立起来的,这期间,中国戏剧导演排演外国戏剧作品、吸纳外国戏剧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某种演出原型、思潮流派的想象,乃至误读。
也正是伴随着对外国戏剧的翻译、想象,一批汲取了外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养分的国内戏剧编剧、导演,开始将中国民族化的审美表达与西方剧场观念相结合,以启蒙与理性为武器,投身于话剧现代化的变革潮流中,推动着话剧剧场美学的新变与重生,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话剧的“黄金时代”。
而中国戏剧探索者身上那种敢为人先的创造激情、昂扬蓬勃的思辨意识、不拘一格的革新精神,则与那个时代一起,成为后人追忆、品评的对象。在经历了90年代至新世纪头十年一段发展的徘徊期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外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外国戏剧进入中国的渠道发生了显著变化。
除了传统的外国剧本、理论译介,以外国剧目演出为主,涵盖教学、研究、制作、管理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外国戏剧引进潮初具规模。从最初的政府交流项目,到民间引进渠道的放开,直至今天多领域外国戏剧引进状态的形成,依傍政策、市场、观众的多重因素,“外国戏剧”不再仅仅是书本上的名词、概念,它变得真实可感、有形有色。
特别是近两年,外国戏剧演出数量迅速攀升,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统计,北京2015年国外戏剧类演出场次达362场,比2014年增加142场。外国戏剧的大量引进,极大满足了观众对戏剧的审美期待和文化消费需求。

立陶宛国家剧院 陆帕《英雄广场》剧照
从这两年引进的外国剧目看,涉及国家的范围比较广,不仅有传统的欧美戏剧,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乃至非洲戏剧都出现在了国内的舞台上。演出类型也实现了多样化,既有话剧、诗剧,也有肢体剧、舞蹈剧场、NTLIVE等,基本呈现了国外戏剧创作多元化的面貌。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引进的不少剧目实现了与国际戏剧舞台的同步。
比如2015年陆帕执导的《伐木》在中国完成了首演后,又分别赴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和波兰弗罗茨瓦夫国际戏剧节演出;
今年演出的奥斯特玛雅执导的《理查三世》,是2015年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的闭幕大戏,还是今年4月罗马尼亚克拉约瓦莎士比亚国际戏剧节的闭幕演出剧目,8月还将亮相爱丁堡艺术节;
2015年柏林戏剧节上备受好评的《共同基础》《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等待戈多》,今年也会接连登陆上海大宁剧院和北京国家大剧院。
这些类型丰富的外国剧目,不仅见证了中国演出市场渐趋开放的姿态和步伐,而且拉近了中国与世界戏剧舞台的距离。

奥斯特玛雅执导的《理查三世》剧照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如此大规模的引进背后,我们的引进标准和选戏原则是什么?哪些外国剧目是我们本土戏剧土壤最缺失的?
至少目前为止,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答案。很多打着“国际”招牌的戏剧节,大杂烩、拼盘式的剧目安排屡见不鲜,剧目质量也参差不齐,缺少演出的总体考量和艺术规划。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眼光,更需要魄力和坚持。以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为例,该邀请展始于2011年。时年,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樱桃园》《白卫军》《活下去,并且要记住》三部作品来京,震动首都戏剧界。
此后,邀请展陆续请来了“契诃夫国际戏剧节”制作的《暴风雨》、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的《唐璜》、以色列卡梅尔剧院的《手提箱包装工》、俄罗斯圣彼得堡波罗的海之家剧院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法国圣丹尼国家剧院演出的《四川好人》、波兰国家剧院(弗罗茨瓦夫)的《先人祭》、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话剧院的《无病呻吟》、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演出的《俄狄浦斯》等16台剧目来华演出。

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话剧院的《无病呻吟》剧照
邀请展创办之初,由于中国话剧“走出去”的滞后,外国很多剧团对中国话剧了解甚少,选戏过程相对被动,然而,几年坚持下来,这个邀请展创出了品牌,用口碑和硬件赢得了外国剧团的认可,还掌握了引进剧目的主动权。
从演出剧目看,该邀请展看似题材丰富、类型多元,却有自己的标准和定位,即以经典剧目为主,兼具实验色彩和学术研讨价值。
在经典的演绎上,用当下的生存困惑、个体境遇和审美思维“复活”经典,将导演的美学创造和艺术表达建构在经典深厚的人文性基础上,成为这些剧目的普遍特色;
在原创的发现上,来自以色列的《乡村》《手提箱包装工》等作品,情节推进、性格塑造大都依托于对本民族历史、性格、身份认同的深入开掘,如何解开心灵的困惑,展示有思想、有生命且性格鲜活的人成为它们的共通之处;
在舞台的呈现上,没有花哨的技术炫耀,没有华而不实的观念炒作,普遍采用了深入浅出的舞台形式,不仅融入了各民族戏剧表达的美学元素,而且在剧场表达的创新上完成了传统戏剧美学与当代审美趋向的对接,充分考虑到不同层次观众的观赏需求。
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把外国优秀戏剧人对经典的敬畏、对人性的反思、对历史的叩问、对艺术的真诚传递给了中国观众,在开拓国内观众审美视野、提升其美学鉴赏水平的同时,也同国内戏剧创作现状形成饶有意味的“互文”。
如何思考人与剧场的关系,如何实现经典与当下、传统与现代、个体表达与美学期待的有效对接,外国戏剧在这方面的成功实践,正是中国的话剧舞台所缺少的。由此而言,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给我们提供的平台不容小视。

以色列盖谢尔剧院《乡村》剧照
价值:应和着当下对优秀原创作品的期待
由于戏剧交流的相对滞后,过去对于西方剧场的演出样态,我们似乎并没有深入的了解,观剧储备不足,信息接收途径大都来自资料的译介、观摩者的描述,因此,当外国剧目起初以“在场”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时,那种艺术、情感乃至观念上的冲击可想而知。
然而,短短的几年内,中国观众对外国戏剧就经历了从观望到惊羡、再从追捧到理性审视的转变过程,对于西方戏剧舞台上的表现形式、技巧手法也有了更多的适应和判断。
这在剧目的演后反响上体现尤为明显。从最初的众口称赞,到如今围绕同一剧目作品的争鸣、争议,观众对于戏剧的价值认知、审美判断及其背后的美学趣味正变得日益驳杂、多元。
特别是当面对“大师级”的作品时,褒贬之间的观点差异有时还非常大,像2014年的戏剧奥林匹克,在铃木忠志的《大鼻子情圣》演后交流会上,有观众不留情面地对铃木说,他亵渎了自己心目中的经典;罗伯特·威尔逊的《克拉普的最后碟带》演出过程中,有观众用英文脏字冲台上叫骂,轰威尔逊下台。
除了这些火药味十足的争议,更多的争鸣则散布在以微博、微信为载体的新媒体、自媒体空间,以不拘一格的文风和私人化的文本细读延续着这些演出的网络热度。

立陶宛国家剧院 陆帕《英雄广场》剧照
有争议、有争鸣自然是好事,说明观众成熟了、见识广了,大师的面孔也可以在争论中不再那么神秘,但是就时下众多的戏剧争鸣而言,大都还停留在就戏论戏的阶段,论辩双方各自挟持一把尚方宝剑,言辞激烈抢占评论的话语权。
这样的争鸣式评论,对于剧作本身而言,可能会是一次挖掘深度、延展意义的难得机会,但就对其引进的真正价值而言,却往往只能隔靴搔痒。
尤其是对于一些“名家名导名团”的作品,我们的评论似乎更津津乐道于探寻它们在“讲什么”、“演什么”,执著于梳理其舞台演出的每一个细节,展示写作者的“创造”激情与文采,却恰恰忽视了“他们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这么演”,乃至其背后的文化生态问题。
理清这些问题,对于中国话剧的未来发展,显然意义更为现实、迫切。而一些戏剧节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探索,较为典型的便是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创办于2010年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之所以能够持续至今(2013年因资金问题停办一年)形成品牌,获得业内较高的关注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专业化的办节思维与优质化的剧目选择。
每一届邀请展,主办方都会设置一个主题,像2010年的“舞台艺术的拓展,表演艺术的拓展”、2011年的“戏剧到底是什么”、2012年的“戏剧就是游戏”、2014年的“还有戏剧吗?”等,借助主题引导观众对戏剧本体的思考,将戏剧观赏、普及与戏剧思考、探讨结合在一起,提升了邀请展的专业性、规范性。

《四川好人》剧照
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邀请展,剧目的选择至关重要。从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历来邀请的剧目看,欧洲特别是德国、波兰的作品备受青睐,像德国邀请到了柏林邵宾纳剧院、汉堡塔利亚剧院、慕尼黑室内剧院等著名院团的剧目,波兰邀请到了克里斯蒂安·陆帕、格日什托夫·瓦里科夫斯基、热戈日·亚日那等一线导演的作品。
选择德国、波兰的戏剧,而不是美国、英国等商业化、产业化水平更为成熟的国家的戏剧,显然有主办方的艺术考量。这些国家的戏剧在人文精神、现实表达、美学实践上有各自的传统与坚守,他们变革剧场的动力、舞台创新的激情、直面现实的勇气,更多源自丰厚的历史积淀与创作主体的内在驱动,源自创作者心灵自由的激情抒发,以及对戏剧理想虔诚而敬畏的表达。
正是这些综合因素的合力,成就了它们戏剧发展的高度和水准。我们可以将这些“请进来”的优秀剧目当作研究的文本,加以分析、辨识,但是没有必要将它们视为中国戏剧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些作品大都植根于各自国家的戏剧传统,更多从戏剧观念的创造、戏剧本体的认识、戏剧文化的表达等不同方面,启发着我们戏剧发展的某种可能,而这种可能也正好应和着我们对优秀原创戏剧作品的期待。
此外,从目前的演出环境看,面临资本、市场、权力的困扰,把国外优秀的作品“请进来”,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引进方对目前日趋商业化、功利化演出环境的一种反驳。

波兰剧院《先人祭》剧照
如今,中国话剧正处于转型发展的“临界点”:
一方面,演出市场规模不断增大,国家对戏剧创作、评论的投入、关注持续增加;
另一方面,国内原创戏剧、高水平的戏剧演出远不能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由此而言,此次外国戏剧引进潮可谓恰逢其时。对于这些剧目,我们不仅要珍惜每一次观摩机会,细心解读外国同行们的导演方式、表演能力,发现他们创造的“闪光点”,更重要的是,还要善于从这些“他山之石”中汲取前行的经验、启示,找到“闪光点”的光源所在,特别是戏剧创作与一个国家戏剧文化之间的关联。
毕竟多研究研究具体问题,少一些华而不实的喝彩、吹捧,对于目前的中国话剧而言,更为紧迫、实在。

铃木忠志剧团《大鼻子情圣》剧照
方向:给戏剧更多人性反思的空间
健康、稳定、规范的戏剧生态由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多个单元系统组成,涵盖戏剧创作、戏剧演出、戏剧普及、戏剧教育、戏剧管理、戏剧交流等各个方面,体现的是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一个国家戏剧创作的水平、剧场美学的高度,反映着这个国家戏剧生态的整体面貌。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为包括戏剧在内的文艺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也为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生长空间。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戏剧观念、表现手段的更新与物质、资本世界的丰富以及技术的发展并非是同步的,它们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不仅需要物质世界的推动和观众的消费动力,更多还需要自身的文化积淀、艺术传统、审美习惯的累积,乃至整个大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呼应。这是戏剧艺术旺盛发展的客观基础。
时下,很多院团、导演排戏可以说已经不再为钱发愁了,特别是一些政府扶植、打造的演出;同时,剧场建设、技术设备、舞台效果也达到了国际一流,可是具备了这些,就能创作出优秀的戏剧作品吗?

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娜剧院《钦差大臣》剧照
从整体上看,我们话剧创作的艺术标准正在降低,戏剧美学走向碎片化,庸俗社会学、投机主义、实用主义仍然阻碍着戏剧观念的突围,艺术创作屡屡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制衡。
戏剧演出环境商业化、产业化有余,精神性、艺术性上的供给不足,越来越多的戏剧创作正变成戏剧定制,项目化的制作模式让戏剧在近亲繁殖中成为少数人的盈利方式;
演剧追求上,舞台创造的重复性在加剧,导演创新力、想象力普遍衰退,技术主义、形式主义、感官主义泛滥,舞台呈现从节制、含蓄迈向夸张、炫耀;
表演上,表演的门槛在降低,演员对角色的情感投入、对台词的细致拿捏、对身体的节奏把握普遍弱化。如果说声音的缺憾可以用耳麦、音效进行辅助,情绪的酝酿可以借助高密度的煽情和气氛渲染加以烘托,戏份的不足可以用视频、多媒体进行辅助的话,演员思考的缺位与激情的缺失,将使表演失去真实的基础,而一旦这种真实性丢失了,话剧舞台的精气神也将不复存在。
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不应仅仅期待与戏剧界内部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自强不息,更有待于戏剧生态的宏观考量和综合效力,即教育、政策、评论、产业等各方面人文环境的同步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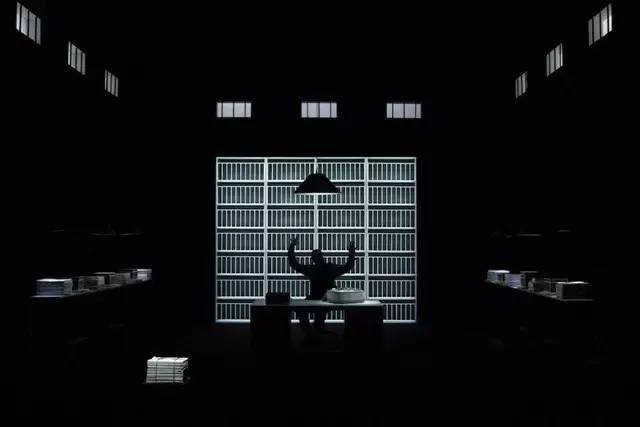
罗伯特·威尔逊的《克拉普的最后碟带》剧照
去年底,笔者有幸受波兰文化与民族遗产部邀请,对波兰戏剧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其间,笔者有幸接触到了波兰戏剧从人才培养、戏剧教育、戏剧研究、戏剧出版到观众培养、剧院管理、节庆组织、戏剧政策等各个环节的专业人士,真切感受到波兰政府、民众对戏剧发展的有力支持和巨大热情,体验到波兰在戏剧文化生态建设上的认真与周全。
可以说,今天呈现在舞台上的波兰戏剧,已经不单单是一次“你演我看”的剧场邂逅,它更像是一场精心准备的文化仪式、一面折射当代波兰世态人情的镜子。波兰的国家面积有31万多平方公里,是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十分之一,其历史同样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的历程,但这个国家的戏剧传统却并没有因为历史的更迭而中断,它产生的思辨力和创造力至今仍为当代欧洲剧场提供革新的思维。
波兰的剧场文化发达,250年的公共剧场发展史,118个全国性的公立剧院,成为这个国家戏剧发展的火车头,每年它们不仅上演着上千部的舞台作品,而且在传承波兰戏剧文化与人文精神上不遗余力。今天我们阐释波兰戏剧,猎奇波兰戏剧的舞台“景观”,不应忽视其戏剧生态的滋润与支撑。

波兰剧院《先人祭》剧照
“世界戏剧已经走得很远了”,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却道出了世界戏剧的发展规律:在变化了的时代面前,尽管遭遇了生存的困惑和美学的危机,可戏剧创作者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传统的戏剧强国仍在不断地砥砺前行。
今天,我们关注外国戏剧引进潮,不是为了提倡中国话剧的全面“西方化”,也不是为中国话剧树立未来的“偶像标杆”,而是希望中国话剧能在其中重新思考前行的方向,少一些好大喜功,多一些沉淀、多一些远见、多一些真诚。
让戏剧回归戏剧,让戏剧与我们的当下走得更近、更真实一些,给戏剧更多思想碰撞、人性反思的空间,这不仅是优秀的外国戏剧探索者们用实践追求的,也是今后中国话剧真正赢得观众认可的正道。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