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森家族与韦伯家族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那时,作为柏林地方政府的一名官员以及民族自由党的党务协调人,老马克斯·韦伯与身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特奥多尔·蒙森结下交情。
老蒙森不仅是一位俾斯麦时代的政治参与者,还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所撰写的《罗马史》至今仍是广受推崇的文本。到了1889年,他甚至还为老韦伯的儿子担任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的导师。
受到父亲的影响,小马克斯·韦伯从一出生开始就被动地介入了政治。从四五岁开始,他就不得不在自家客厅中聆听柏林政治精英们的高谈阔论,这培养了韦伯对于政治话题的强烈兴趣,这种兴趣既是学术性的,同时又有实用性的一面——终其一生,他都在尝试介入政治实践,直到去世前数月依然如此。
蒙森家族则继续钟情于历史学,老蒙森在190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孙子威廉·蒙森同样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而到了曾孙沃尔夫冈·蒙森那辈,则成为了首屈一指的马克斯·韦伯思想研究者。此时的小马克斯·韦伯,早已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德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先驱。
家族间的久远交往不仅给予了小蒙森探究马克斯·韦伯思想形成的兴趣,还提供了真实的便利。他的《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一书成为韦伯研究领域公认的里程碑式著作。2016年,这部作品的中文版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并由阎克文担任翻译。
与大量中国读者熟知的关于韦伯的描述不同,蒙森并未从韦伯的理论入手去解释这位社会学奠基人的理论观点,而是从其生平出发,将韦伯当成一个德意志的政治介入者,理清其政治生涯与学术脉络间的关系。

作为历史学家,蒙森精研19、20世纪英国与德国政治史,同时还广泛涉猎外交史、社会史、思想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他从广阔的视野中充分汲取材料,大量引述、分析韦伯公开发表的著作,以及无数散布在档案中的草稿、书信、演讲、会议发言、报纸报道,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整勾勒出了韦伯自青年时代开始近三十年的政治思考轨迹。
在研究过程中,蒙森敏锐地发现,尽管韦伯从青年时代就与盛行的俾斯麦崇拜保持距离,并对其权力政治遗产带来的社会后果发出了毫不留情的道德批判,但对于俾斯麦缔造了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韦伯从未吝惜赞美。某些程度上,“不忘德意志民族历史使命”是韦伯生命中的一大主题。
人们总是易于忽视,马克斯·韦伯仍然是威廉时代的德国知识精英,他一直抱有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及至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魏玛共和建立,韦伯仍然主张宪制改革应该为德国总统提供类似立宪君主的地位和权力。
蒙森从技术手段上审视韦伯的这类念头:“他的观点并非保皇主义情感的反映,他对君主制的支持乃是出于选择最佳治国技术的功能考虑,根本不意味着情感上的忠诚。他相信,一个‘强大的议会君主制’在技术上最有适应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归根结底它是最强大的政体。它优越于所有共和政制之处就在于,它是奠定在一个重要的形式优越性基础上的——‘国家的最高职位已被永久占据’,因而对抱有个人野心的政治家的权力欲构成了健康有益的限制。”
这个推论隐藏着两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一方面,韦伯毫无疑问是来自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同时还是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坚定支持德国的强权政策与帝国主义扩张。另一方面,韦伯鼓吹议会民主体制,但这并非因为他相信民众当家做主的可能,而仅仅是出于民主制度对他而言是一种利于发展民族国家的实力与声望的工具。
韦伯欣赏卡里斯玛型领袖,在他看来,最好的民主形式是使得政治家利用民主过程取得民意支持,实现“民意认可的领袖民主制”。
关于这种观点,蒙森在书中使用了一段发生在马克斯·韦伯和鲁登道夫之间的谈话资料加以佐证。在这段对话发生前,韦伯要求战场上面临败局的鲁登道夫提着头向协约国自首,挽回德国的荣誉:
鲁:“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兴登堡?毕竟他才是德国陆军元帅。”
韦:“兴登堡已经70岁了,而且连小孩子都知道,你才是德国的头号人物。”
鲁:“敬谢谬奖。你可是为民主唱赞歌的,你和《法兰克福报》应该受到谴责!你看看,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韦:“你觉得我会把现在这种丑恶的动荡叫作民主吗?”
鲁:“那么你的民主是什么样?”
韦:“人民选择他们信任的领袖,然后被选出来的人说,现在你们都闭上嘴,一切听我指挥,谁都不许随便干预领袖决策。”
鲁:“我倒喜欢这样的民主!”
韦:“但人民会坐下来看热闹,如果领袖犯下罪错,就把他送到绞刑架上去!”
这类无情的剖析和举证使得《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第一版在1959年出版后引发了德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弹。
作为失败了的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国,新一代的德国学者在战后将20世纪初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韦伯视为德国民主传统的先行者,然而蒙森的拷问打碎了这一幻想。韦伯在魏玛共和前期对于“真正的政治家”的呼唤,很难不让人联系起在其身后出现的纳粹德国。尽管,韦伯在任何意义上都绝对不可能会是希特勒的支持者。
就连雷蒙·阿隆也发出感叹:“把韦伯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立场称之为他的基本政治立场,必定会产生令人恼怒的影响,而证明马克斯·韦伯支持议会民主秩序是为了服务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权力,这尤其会令人激愤。”他一针见血指出这部作品对于德国知识分子的伤害在于“新生的德国民主失去一位创始人、一位显赫的鼻祖和一位天才的代言人”。
直到今天,韦伯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这一问题仍然在知识界受到讨论,由于韦伯认为国族的发达与个人的自由这两项价值不可偏废,这类争论似乎不可能产生终极的结果。
但在蒙森看来,韦伯终究没有维系住自由主义价值的独立与优先,偏向了民族主义,成为一个“灰心的自由主义者”。
但不过蒙森再三说明,韦伯的民族主义并不单纯以民族的壮大这件事为终极目标。这使得他的政治理论区别于任何旨在穷兵黩武的沙文主义。他不但将种族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抨击为“绝对空洞无物的动物学民族主义”,也鄙视盲目俯首于权力。他在德国战败时渴望有领袖型人物出手整合这个溃散了的民族,但对于只知炫耀权力、耀武扬威的政治强人或强权国家,韦伯并无好感可言。
在他眼中,德国的崛起与势力的扩张,甚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主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国家能够获得的政治与经济上的收益与损耗,而在于地缘政治的结果会促成什么样的文明得势,什么样的人格与文化在将来的世界取得支配地位。
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政治观,促使韦伯从学术生涯的早期就不甘于仅仅作为一个学者。许多接触过青年韦伯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天然的政治家”,应当责无旁贷地投入政治实务。韦伯本人也曾相信如此,他从1895年开始,直到魏玛制宪方案确定,韦伯参与其中并留下了许多备忘录。
但正如蒙森看到的,“如果把韦伯看作一个眼光深远、头脑冷峻的战略操作大师的话,他在日常的战术操作层面却完全是个手足无措的外行。他深知现代政党组织的功能主义价值是多么不可或缺,但在那种极度撕裂的政党政治格局中,他对组织的经营与整合却一筹莫展,甚至不屑一顾。”
韦伯早年受到过卡尔·马克思的影响,但很快,韦伯就对一元化取向的决定论产生了毫不妥协的敌意,他认为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都难以作为有效的理论手段胜任实证性的经验分析。
真正对青年韦伯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滕,他是老韦伯的好友,更是个欣赏自由主义的人物。从鲍姆加滕那里,韦伯获得了不少启发。比如在看待德意志传统时,他没有片面看重普鲁士的分量,还尽力不忽视南德的自由传统。这种多元思考使得韦伯能够清晰看到德国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群体政治不成熟的问题,并将其归因于俾斯麦统治的影响。
当魏玛制宪方案开始讨论时,韦伯试图在这一历史关键节点中获取自己的政治地位,但他发现,自己必须与僵化的政治教条和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作斗争,这实在非其所长。他对政治架构的理解与思考如此深入,但德国国民的政治教育被耽误太久,使得韦伯“看上去就像一个伟大的军事统帅,但身旁却没有一兵一卒”。
也许历史永远不会给理想的政治家机会,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后人对马克斯·韦伯的判断,这位威廉时代的德国知识分子亲历了欧洲旧秩序的衰亡,他用一生汲取关于世界政治的知识,这使得他拥有古往今来最强大的政治头脑之一,尽管他的政治观点仍有时代束缚,尽管他的日常政治手腕难以支撑自己的战略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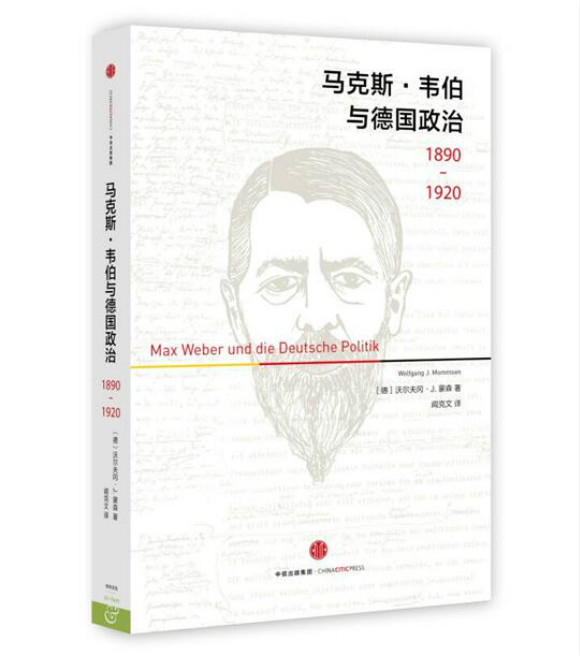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