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真的诞生在雅典城邦?
议会制度真的是英国送给文明世界的礼物?
为什么妇女在远离现代欧洲权力心脏的地方更早地赢得了投票权?
如果在不久的未来,民主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枯萎了、消失了,那会怎么样?
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John Keane)在《生死民主》中向关于民主的起源、含义和当代意义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他描述了民主诞生时千差万别的历史背景,追溯了民主不断变化、备受争议的含义,解释了现代民主为何以及如何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传播。
克里斯提尼、弥尔顿、甘地、罗莎·帕克斯以及那些几乎被人遗忘的民主捍卫者——开创政党政治的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主张废除奴隶制、呼吁妇女投票权的安吉丽娜·格里姆克等——轮番上场,公民大会、代议政府、菩提民主、强人政治、陪审团、出版自由等概念见证民主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全球发展。民主的脆弱性和偶然性通过众多历史事件呈现出来,基恩强调,当今世界的监督式民主来之不易,而民主在未来仍有可能滑向深渊。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节选了《生死民主》的尾声部分,以期与读者共同反思民主的来源、价值与危机。

《民主这个东西》(节选)
2003年秋季,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的一个阳光耀眼的葡萄园里,这些长老们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在美国率领占领军推翻了当地的塔利班专制政权之后,阿富汗人如何开始走向选举民主。这样的会议在当地被称为“舒拉”(shura),意思是“政治协商会议”。
如果在不久的未来,民主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枯萎了、消失了,那又会怎么样?在现在的世界上,对于如何掌握权力,人们有很多的选择,从鬼祟的私下交易,到蛮横的拳脚和炸弹,监督式民主不过是其中的选择之一,而且不是什么非有不可的东西,难道不是吗?它真值得人们挺身为之而战?真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准则,不论是坎大哈葡萄园里的人,还是黎巴嫩贝卡山谷里的人,或者法兰克福、东京和莫斯科的工人,台北和开普敦的商人,印度的女贱民,中国的农民,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甚至那些大国际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都能够接受和适用这一准则?或者说,究根结底,民主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虚假的普世标准——正如尼采所说,是那些花里胡哨的西方价值之一,这些小把戏不过是为了哗众取宠,欺骗人民,让他们相信这件东西不是权力的一件外套,不是主子们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难道不是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至少决定了是否能改变反民主派的观念,但寻求答案的努力面临一种非常古怪的局面:在监督式民主诞生半个世纪之后,全世界的大多数政治评论家都在回避人们是否有追求民主之愿望的问题。在这个民主正在享受各种创新的关键的历史时刻,人们却反常地对这个题目保持了某种令人不安的道德缄默。不错,记者、公民活动家、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通常都承认,民主正在第一次成为一种世界语言。他们经常说,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从印度到台湾,从埃及、乌克兰、阿根廷到肯尼亚,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了一套民主的词汇。有些智库的报告颂扬民主,寻找证据证明民主是势不可当的大趋势,民主的支持者则从这些报告中寻找精神支持。很多人因此而坚定了自己对民主作为全球价值观的信念。虽然,那些内行的人明白,民主是一种特殊的理念,有其特殊的地缘渊源,发端于古代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早期希腊城邦,他们还是给出结论说,民主业已战胜了所有其他的政治价值。民主已经成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似乎成为全世界追求的普世生活方式——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有句名言说,它是“一种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会视为珍宝的普世价值”。
这个观点首先遇到的麻烦就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民主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民主的敌人势头正在上升,甚至那些对民主抱有某种认同的评论家和领袖们,对于民主是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生活方式这一说法,也都公开做出调侃的姿态。美国外交家、“冷战”时期的政治顾问和著名学界领袖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1904-2005)曾经说过:“我知道,没有证据说 ‘民主’,或者我们根据自己的生活对这个字眼的想象,是大部分人类生活的自然状态。”凯南认为,民主“不过是一种管治形式(而且是一种相当苛刻的管治形式,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西北部演化生长……逐渐被带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北美。而北美的居民还是来自欧洲西北部的移民”。这种思想方式表示,民主是一种具有地理特性和时间限制的理念,仅仅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域,被某些人民所接受;因此,应该反对任何推动民主,将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企图,这些倾向总是傲慢、让人厌恶。凯南总结说:“恶政,以决绝、专横,甚至经常是残酷的手段争夺权力,是绝大部分人类过去数百年和数千年的常态。不论美国人的’风车大战’如何英勇卓绝,这一状况在未来将长期持续下去。”
认为起源于希腊或西方的民主绝对是特定历史时刻和特定地理条件下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信条可以有若干并且相互冲突的用途。比如,它可以得出某种非常痛苦的结论,说世界命中注定只能有一半的地方实行民主,有些幸运的人民可以享受硕果,而另外一半倒霉鬼只能在那些有一点民主或者毫无民主的地方忍气吞声了。民主只是特殊地理条件的产物,因此不可能是全球的道德准则。当然,这个结论可以让有些人欢欣鼓舞。在迪拜和多哈这样的产油国消费天堂里,富豪们通常都轻蔑地表示,民主是过时的老货色了。那些优雅地生活在衣香鬓影、美酒佳肴中极端西化的俄罗斯资产阶级对中东石油大亨的见解表示赞同。如果问他们怎样看待民主,他们会回答说:“民主吗?为什么要民主呢?德国人自由吗?美国人自由吗?”如果你告诉他们,在这两个国家,人们至少可以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有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有独立的司法,那么,他们会回答说:“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民主。这样的民主意味着俄罗斯的灭亡。我们的人民压根不喜欢民主。”废话少说。如果还要继续追问专制政权下是否可能存在自由,那简直就是没有礼貌,这样粗鲁的提问,干脆会被人嗤之以鼻,受到嘲弄。他们说:“这里的人什么都不会放在心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有独裁,我们也有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能进行自己的选择。”
更令人好奇的是,认为民主是地域特产的观点,也可以煽动完全相反的情绪:必须推翻独裁。此类分析的逻辑是,如果说民主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它不过与其他众多的价值观一样,那么,谁有实力,谁就可以成为风行世界的主流。这样的说法够机智,而且很可能也是对的。以著名的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对民主所做的解释为例,他和凯南一样是不喜欢咬文嚼字的人,他直截了当地说,现代代议民主是“北大西洋文化”的“特殊产物”,它绝非终极价值,从哲学意义上看,它既非“真”(True),亦非“理”(Right),也不“普世”(Universal)。但是,当人们追问,为什么他认为“北大西洋”的民主尝试为人所追求时,他总是立刻回答说,应该彻底抛弃普遍追求民主的推论,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大家都认为如此”的东西,同时他又说,民主不需要从哲学上为自己寻找证明。他说,如果民主不去张扬道德的旗帜,反而能够轻装前进。他们没有必要去拉扯那些晦涩的理论,不妨拿出“哲学肤浅和头脑简单”的派头,坚持自己的信念,一路向前推进。罗蒂相信,民主不是神学或什么形而上的替代品。民主的理想为人所追求,不是因为它与既成“存在”的呼应关系,它不是无可逃避的必然,绝非只需要我们承认或服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按照罗蒂的意见,所谓民主具有“道德优越”皆因它是一种“追求希望的积极文化——希望通过此时此刻的政治和社会努力,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与东方文化消极退却的特点正好相反”的观点,以及诸如此类似是而非且毫无必要的哲学议论都应该被抛弃,没有必要将这些陈旧的道德说教作为民主的起源或推行民主的动力。尽管民主只是诸多价值准则之一,一旦进入实践,它就能自证优势。在小布什总统发动反恐战争之后不久,罗蒂评论说:“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西方基本上在正确的轨道上。我不认为要有什么向其他文化学习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就是扩张,就是西化整个地球。”
通过民主化来西化整个世界:在我为这部民主史的写作进行准备之初,我与罗蒂在一次早餐时讨论过民主具有的潜在的积极影响,他耸了一下肩膀后才开始发表意见,这几乎成了他的标签。他同意,我们就民主所做的争论,都建立在民主可能带来有益成果的假设上,而实际上这个假设却非常不可靠。我们两人一致认为,那些出于结果论的理由而赞成民主的人,通常都试图说服别人民主比其他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某些目标,他们说,民主的正当性来自它的实用性、操作性和实践性。比如,有人表示,民主是一种优越的管治形式,因为它将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最大化;另外一些人说,民主的优势在于它培育了强调正义的发展方式,这正是印度学者拉基恩·科塔里(Rajni Kothari)坚持的观点;有人夸夸其谈,说民主之所以优越是因为它比其他体制更能刺激经济增长;还有人声称民主可以驯服战争之兽——它培育“民主和平”——或者它能减少所谓“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止如此,美国研究民主的老一辈思想家中有些人,比如罗伯特·A.达尔(Robert A. Dahl)强调,与其他任何现实的制度选择相比,民主能让“人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我们两人都同意,这些观点中绝大部分都是像是狗在追赶自己的尾巴,是些没有意义的命题。比如,说民主优越,因为它为人民参与公共决策清除了道路,实际上这等于是说民主之所以优越是因为民主优越。所谓民主促进人的发展(或人本主义等)也有同样的问题。此外,我们都认为,当开始考虑现实的可行性时,所有关于民主普适性的观点都变得极其可疑。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民主制度可以一贯优越于独裁统治;而“人类发展”的性质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以及什么是“国家安全”本身,已经有太多没有解答的疑问。所以,罗蒂同意,这些民主观非常含混不清,很容易被人指为和稀泥,甚至是虚伪,它们对民主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它们对民主的支持。此外,20世纪末出现的“协商民主”论也未能消除现在这些民主论的危害性。且不说它未能回答协商民主是否和怎样能通过代议民主制度让自己得到最大发挥的战略问题,自我标榜的“协商民主派”在赞扬民主理念的时候,说它要求人民在投票时认真考虑其他人的意见,而不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断定什么选择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为什么公民们的行动一定要深思熟虑、及时和负责任?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公民的行动算得上是深思熟虑、及时和负责任?为什么协商原则应该成为普世的准则?……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迄今为止,“协商民主”受到追捧,似乎就是因为它将协商最大化,也就是说,它确实能够让公民们卷入各种没完没了的协商工作。
这些思想和理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当我们俩的早餐对话快要结束时,罗蒂确实提到,他主张民主,认为民主是西化世界的各个角落所共同追求的价值,是因为民主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一种希望,即人们可以从暴力和残忍的诅咒中解脱出来。是说服而不是强迫,是妥协和改革而不是血腥的革命,是自由和公开的对抗而不是欺压和霸道,是一种开放的、实验性的思维模式——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明白,他这种一厢情愿的改良主义算得上是美国当代“推进民主”的努力及其军事行动的同盟军。罗蒂式的世界实用主义绝不是天真无邪的东西,它可以,而且也确实在魔鬼的游戏场上与暴力裹挟在一起,比如我们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命运多舛的民主尝试中所见识到的景象。到2006年7月,阿富汗新出炉的议会里,绝大部分议员(比如阿梅德·瓦利·卡尔扎伊)都和军阀、毒枭、迫害人权行为拴挂在一起,出行时要乘坐加重的装甲车辆,跟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时刻要躲避各种威胁和敌人对他们性命的悬赏(打死奖励25000美元,活捉奖励50000美元)。
说到民主优越的实践性,武力的支持总是会让民主背上恶名。在21世纪初,确实产生了某种“民主挫败”(democracy pushback),比如我们在中东很多地方所看到的情况。黎巴嫩德鲁士族(Druze)领导人和议会反对党议员瓦利德·贾马布拉德(Walid Jumblatt,1949—)严厉斥责美国的民主推进行动,只要民主盲目和傲慢地自认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北大西洋”价值,贾马布拉德的话就可以被视为是民主的凶兆。他说小布什总统像是一位“丧心病狂的皇帝”,一位自以为是的“上帝在地球上的副手”,他说康多丽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脸上涂抹了一层“油漆颜料”,说托尼·布莱尔是一只“有恋物癖的孔雀”,贾马布拉德讽刺地将民主定义为一种帝国政府,“他们的天空就是美国的飞机,他们的海洋就是美国的舰队,他们宅基就是美军的基地,他们的政权就是美英统治,他们的河流就是美国船只,他们的山峰就是美国的突击队,他们的平原就是美国的坦克,而他们的安全就在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这类攻击自有其政治目的,这类攻击尽管粗暴自负,却提醒我们,那个天真地相信民主的时代已经终结。也许,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这些谴责揭露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冲突:事实上,那种坚信“北大西洋文化”或者“西方”(不管它如何定义)对民主理念拥有专利,认为这种理念值得提倡,甚至使用武力进行推广的想法,都是政治傲慢和自相矛盾的教条。民主成为一副救命方剂,可以由一个人开方,施用到另一个人身上,尽管事实上这些药味道古怪、令人厌恶,甚至让人作呕。
民主能够避免这种自相矛盾吗?面对21世纪的反民主的潮流以及对民主的疑惑,民主党人是否能够找到一套全新的话语来谈论民主的全球优势,保护民主的伦理?或者说,民主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的理想,被一些权势政客拿来招摇撞骗,谋取私利?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那些仍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即民主真的是一种普世的理想,适合世界上所有的人民,而不是一种强人或莽汉对付弱者的借口?民主的理想能否民主化,走向平民大众,丢开那些激昂躁动的说教,更谦卑、更公正地服务大众?回答是民主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民主远远不止于过去那个美好而令人向往的理想,我们需要对民主进行一种民主的,至少比以往更加民主的新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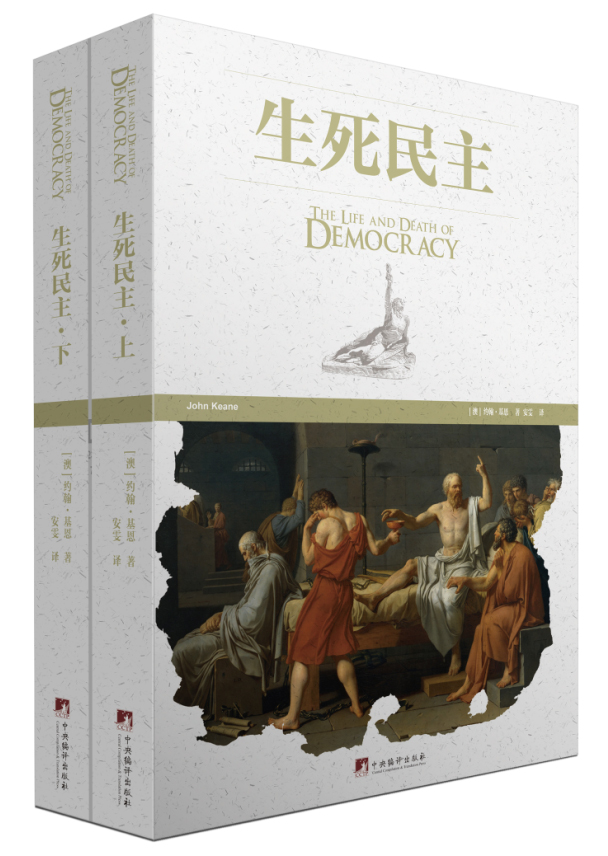
……………………………………………………
欢迎你来“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找我们。
(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