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纸媒的时代过去了,门户网站只靠PC端内容也不再能聚集流量……但祁又一并不是唱挽歌的人,他曾在微博中写道,“从某种角度讲,我这人一生都在学习如何变得和别人一样。”随着流媒体逐渐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祁又一做起了播客节目《摇滚又一榜》。
不过祁又一也有困惑,就像所有经历过时代阵痛的知识分子,他们一面被时代推搡着向前,一面又希望能留住些永恒不变的东西。至于这个“永恒不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现在的祁又一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如果我写作特别顺利的话,可能压根也不会做这些事了。”
文丨李禾子
编辑丨于墨林
1
《摇滚又一榜》在网易云音乐上线的时候,已经是祁又一入行的整整第十年。
2003年,祁又一找到了自己生平第一份“靠写字挣钱”的工作,在《精品购物指南》文娱部做音乐记者。 当时的祁又一还在读大三,虽然因为新概念作文比赛被保送进了北师大中文系,也一直被当成作家培养,但自觉成为职业作家无望的他最终还是选择进入了媒体。在《精品》的记者生涯也重塑了祁又一对未来的期待,“当时希望自己能把报道的工作一直做下去,而且是以一个乐评人的身份。”
准确地说他既做记者,也做编辑,报纸的音乐版块于是成为了他的一块自留地。“那段时间写了很多关于摇滚乐的东西”,祁又一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二篇文章就写了窦唯。虽然这些内容和消费导向的《精品》多少有些气质不符,但后者依然给了祁又一足够的自由度。
直到2005年选秀节目风靡全国,报社也出现了转向,“大领导是李宇春的著名粉丝,实在没办法在一块工作了。”2006年9月,为了新闻理想,祁又一离开了工作了三年的《精品》。
从那时起,祁又一认为《精品》的黄金时代过去了。那个“黄金时代”几乎奠定了他日后的职业基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认识了很多靠谱的人”。

2
祁又一在报社工作的几年也正值中国摇滚乐最低谷的时候,“感觉(摇滚乐)马上就要完蛋了,根本没人去看演出,液氧罐头、AK47这样的主流乐队,演一场台下可能也就2、30人。”所以祁又一一边做记者,一边还组织起了系列演出。
这些演出有一个好玩的名字“小朋友的偶像par”,并且全部免票。做这样的免费演出需要打通场地、乐队和乐迷。因为做记者的缘故,祁又一和当时很多酒吧老板的关系都不错,“我就和他们说‘能不能别要我场租,我把观众招来,你们卖酒水’”;至于乐队,“我就说‘你们演出费降一点,我全掏了,也不用跟酒吧分门票了’”;能免费观看演出,乐迷自然也很乐意。
演出不仅招来了很多乐迷和自己一起pogo,组织团队也慢慢壮大起来,雷子、郭小寒、刘颖和张帆也都加入进来。“我后来连钱都不用掏了,只负责把乐队招来就行。”祁又一说。
2004年起,从无名高地到13club,从痛仰到重塑雕像的权利,“小朋友的偶像par”前后一共办了将近20场演出。即便不赚钱、倒贴钱,祁又一和大伙儿也都乐在其中。
那时的祁又一还做了太多不赚钱的事,譬如志愿做迷笛音乐节新闻官(2004年),创办非营利性唱片厂牌LUDI(2007年)。“我们相当于给行业打了一剂强心剂,”祁又一没把赚不赚钱的问题看得太重,“这些都是很松散的事,也没遇到过什么困难,只要跟挣钱有关的事情都会遇到困难,不为了挣钱反而会有很多人来帮你。”

3
从《精品》辞职后不久,07年祁又一又入职新浪,一手创建了新浪摇滚频道。
“IT公司和原来《精品》散漫的风格差别还是挺大的。”这是他入职新浪之后的第一感受。虽然接受了新浪坐班的要求,但祁又一更愿意用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我实现更大目标的同时,也能给公司带来效益。所以我并不是单纯为别人打工,写作也不是为了别人能给我发工资。”
不论如何,新浪摇滚频道还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施展空间。新浪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家开通摇滚子频道的主流网络媒体,也是很多摇滚音乐人及乐队主要的宣传渠道。因此,新浪摇滚频道成为很多乐迷获取相关信息的唯一来源,可以说自带“独家”属性。
“那个时候的媒体和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祁又一感叹。不同在哪?十年前他每发一次报道、每写一篇乐评,即使不做推广也一定会有关注,现在却不一定了,“确实是时代变了。”
4
从《精品》确立起的职业理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纸媒的时代过去了,门户网站只靠PC端内容也不再能聚集流量……但祁又一并不是唱挽歌的人,他曾在微博中写道,“从某种角度讲,我这人一生都在学习如何变得和别人一样。”
2013年,随着流媒体逐渐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祁又一转而做起了播客节目。“做这件事不会牵扯自己太多精力,又能有一个说话的地方,还挺好的。”这就是《摇滚又一榜》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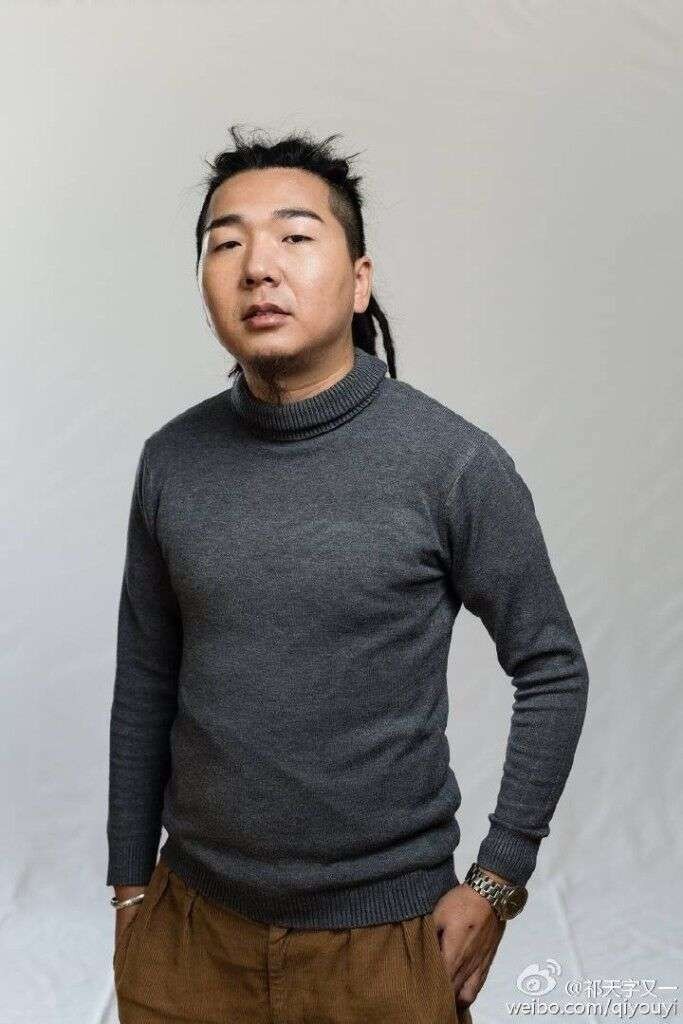
在行业十年积攒下的人脉和资历,让《摇滚又一榜》从来不缺内容,谢天笑、脑浊、痛仰、二手玫瑰……这些已经成为中国摇滚乐中流砥柱的乐队和音乐人,都成了祁又一节目的座上宾。目前节目已经做了357期,且每期的播放量一般都维持在1万次以上,梁龙那期还创下了10万的播放记录。不过祁又一并不会太关注“播放量是否又创了新高”这类问题,他对这档节目的核心价值有着明确的判断,就是“真实”。
让他印象较深的是去年和有待一起录的节目。在此之前,《摇滚又一榜》的节目形式均为“访谈+榜单”,祁又一会在每期节目录制前从微博和微信统计好听众票选出的前十名歌曲,在节目中播放。但是在和有待聊天的过程中,他发现“不用播歌了”,两个人聊得起劲,一直录了3期。祁又一笑说这期节目特别具有“史料价值”。自那之后,节目改成了“纯聊天”。
不过,祁又一也一直没断过做排行榜的念想,“应该是有排行榜的,我希望把这个节目真正做到有权威性的时候,再把榜单恢复。”他指的“权威性”并不是针对大众,“所有排行榜都有编辑个人的操作艺术在里面,我不希望它太大,而是有一个固定的风格,并且保持独立和中立。”在他的设想里,未来最好还能在年底举办例行的颁奖典礼。

5
祁又一也有困惑,他常常会反思自己是不是在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上把握不对。节目是不是该建一个微信群呢?是不是该转成视频节目呢?是不是该放弃独家全网上线呢?
他更大的反思还是对于时代,“我有一种感觉,现在人们并不会太在乎你卖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价值,而在于你卖的手段是什么。对于我本身,我认为自己长期积累了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一个新的推广方式……问题就在于,现在这个时代推广的门槛提高了,你必须达到一定的及格标准,大家才会进行筛选,才有可能分成不同的层次。”
《摇滚又一榜》现在只有祁又一和他的助理两人在打理,但是想把节目做大,资金和团队都是问题。“自媒体没有一个团队也不行,”祁又一希望自己别再单打独斗了,“但这事说它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很多互联网传媒公司都在做这个,可是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就很不容易。”
就像所有经历过时代阵痛的知识分子,他们一面被时代推搡着向前,一面又希望能留住些永恒不变的东西。至于这个“永恒不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现在的祁又一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如果我写作特别顺利的话,可能压根也不会做这些事了。”

平时喜欢看什么书?
Q:平时喜欢看文字优美、完成度高的书。我想不管小说还是社科读物,文字优美都是一个充要条件,就像古时候的人除了文字优美还要看你书法如何呢,是一个写作者的修养问题。具体一点说,最近在重看《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目前为止让你感觉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Q:我刚入行的时候,大概22、3岁,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酒吧一块喝酒,然后崔健来了。当时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他真的是把我当朋友,并没有敷衍我。这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到现在我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后来我去采访他,他送了我一张签名唱片,这些对我来说都特别珍贵。
你认为天赋和后天努力哪个更重要?
Q:我认为一个人只要努力,进入专业层面肯定没有问题;一个人想大出师,成为业界翘楚就不一样了,除了努力还需要天赋。
你典型的一天如何度过?
Q:早晨起床将孩子抱到客厅交给阿姨;做一套瑜伽;吃早饭;打开电脑开始写作;吃午饭;睡一觉;继续写,并开始联系朋友,看晚上跟谁去哪里玩;约不到人在家喝酒看电影,约到人晚上出去玩。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