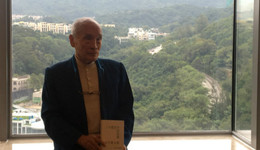外国文学
巴特勒认为,特朗普连续发布行政命令的举动,正是专制政府正在一步一步测试其权力的极限,企图推翻法治。
庄佳怡 · 03/22 11:00
这些故事精准捕捉了当下的互联网政治,“在网上,被拒绝的个人感受会迅速扩大为一种世界观,甚至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仿佛整个宇宙都在恶劣对待你这个个体。”
王鹏凯 · 02/22 11:00
许多年来,萦绕在2024诺奖得主韩江心头而始终无法得到回应的问题就是,“世界为何如此暴力和痛苦,世界为何又如此美丽。”
上世纪80年代,施瓦辛格、史泰龙等占统治地位的明星,被更年轻纤瘦的约翰尼·德普、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等人抢过风头。由此可以看出,流行男性气质的变迁与现实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存在着某种关联。
《百年孤独》在哥伦比亚国内引发热情响应,社交媒体遍布相关讯息,政府还专门为此组织了一条马孔多旅行路线,希望这部剧能像《权力的游戏》一样吸引更多读者和观众来到哥伦比亚旅游。
作为一个“阶级变节者”,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充满疑问、愧疚、羞耻、自我诘难,并试图写作穷人的故事,挑战生活的政治。
在随笔集《一个人生活》中,谷川曾风趣地思考生死之事:“对我来说,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情是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了,而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事是我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