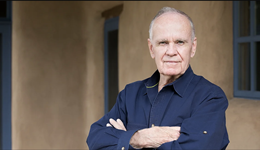逝者
麦卡锡的作品中充斥着黑暗和暴力元素,这是因为他不认同“人类可以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好,然后每个人都幸福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这种想法,他认为一个人越是渴望这种生活,越会让他成为奴隶。
叶青YQ · 06/14 10:41
“你通过我的文字或影像,你会觉得作为人,本质上和你们也没有多大区别。我可能更了解他们作为人的最细微的情感方式。”
董子琪 · 05/09 09:40
坂本龙一的音乐广博、大气而难以定义,甚至不总是悦耳,但也正是这些“不悦耳”印证了他以音乐介入现实的力度和决心。
如何使个人的痛苦和大众的痛苦乃至人类的苦难建立联系,如何把对自己的关注升华为对苍生的关注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具有普世的意义,大江先生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
王中忱认为,大江首先是在一种否定的精神状态中和萨特获得共鸣的。他在少年时代经历过“帝国日本”的思想禁锢,战后也不断体会到日渐保守的日本社会的压抑,“在如此处境之中,他从萨特文学里汲取启迪和灵感,无疑是非常自然的。”
 |
|